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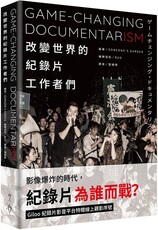

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
作者:someones garden(編者) 出版社:行人 出版日期:2021-12-30 00:00:00
<內容簡介>
約書亞‧奧本海默拍出震撼世人的紀錄片《殺人一舉》、《沉默一瞬》,試圖釐清1965年印尼「清洗共產黨」的血腥鎮壓歷史,卻從此被印尼政府限制入境。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吹進東南亞,克里斯.凱利不顧自身安危,緊隨著金邊居民完整記錄他們面對暴力徵收、拆遷時捨身取義的抗爭行動,完成典範之作《柬埔寨之春》。
「渴望改變的信念, 不會輕易被擊潰。」
紀實、顛覆、煽動、見證、傳達……紀錄片反轉觀點、改變世界之作還有更多:小川紳介以日本成田機場三里塚抗爭系列紀錄片影響了全球影像工作者,甚至催生出「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無國界醫生組織在前線為醫療奮戰不懈,同時藉影像記錄作為見證,讓世人得知戰地真實。
《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一書從「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形容大膽祭出轉捩策略時使用的「Game-changing」,與紀錄片主義「Documentarism」兩字相結合的本書自創詞──發想,以「改變世界」為主題深入訪談,探詢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推動紀錄片工作者們奮不顧身完成作品,讓觀影之人如我們都因此被震撼心靈,產生共同信念:「努力記錄眼前現實情況的紀錄片,其中必然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本書這些人與作品再次定義了紀錄片,從中展現全新意義。其中包含:
導演阿比查邦(《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華麗之墓》)、
導演拉夫.迪亞茲(《驕陽逼近》、《悲傷祕密的搖籃曲》)、
導演原一男(《怒祭戰友魂》)、
社會運動者卡勒.拉森(「占領華爾街」行動)、
劇場導演高山明(《麥當勞廣播大學》)、
紀實攝影師亞雷希奧.馬莫(「為所有戰爭而存在的醫院」)……
以及重要紀錄片提案暨論壇主持者、影展策展人等,超過30名以上知名導演與相關工作者的深度訪談。另收錄日本紀錄片實驗祭典「Docu Memento」裡,新銳導演們的創作歷程圖表。
本書發想與編著者「SOMEONE'S GARDEN」,為日本知名藝文團體,從事雜誌、書籍的編輯、設計、app、影像製作、活動舉辦等相關藝文工作;成員為藝術家津留崎麻子,與雜誌編輯西村大助。團體「BUG」作為編輯協助,是由日本一群身懷使命感的紀錄片工作者組成,具備設計師、哲學家、編輯者多元身分;其舉辦的獨特祭典活動Docu Memento,邀請被視為社會問題的當事人、分享計畫的紀錄片導演,用自己的語言提出訴求與想法。透過兩個團體合作,展現出《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一書與眾不同的多重觀點與當世意義。
影像科技迅疾發展的時代,每個人都有機會透過手上的3C產品拍下紀實影像並擴散。當我們深入討論紀錄片的形式與功能,以釐清這些作品輕重之時,導演晉江在本書內闡述:「紀錄片是一個愛的過程。」藉著這句話,好像更容易理解何謂紀錄片。《翻滾吧!男孩》裡我們看見導演對體操孩子們的關懷,甚至在16年後親眼見證主角拿下奧運奬牌;透過紀錄片《時代革命》、《理大圍城》,我們感同身受了抗爭民眾對香港深刻的愛……面對紛擾之年,藉由《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我們重新體認觀看現實的多重方式,看世界如何被這些作品與人改變,或,有機會,我們將能如何改變這世界。
與Giloo紀實影音平台獨家合作,隨書贈送30天線上觀影序號
關於 Giloo紀實影音:
Giloo的命名,來自於「紀錄」的發音,是台灣唯一以影展及議題為導向的影音平台,搜羅台灣與全世界最重要的電影,打造專屬於影迷的文化社群。
線上觀影書中大師級作品《柬埔寨之春》、《龐克海盜地獄首爾!》、《不丹少年轉大人》 、《1428 》......等,顛覆你對紀錄片的想像。
★本書特色:
●與Giloo紀實影音平台,獨家合作線上觀影活動
●集結約書亞・奧本海默、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克里斯.凱利等全球著名導演專訪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翻滾吧!男孩》、《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紀錄片導演好評推薦!
★名人推薦:
——影視界、媒體界工作者好評激推——
王祖鵬|地下電影
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資深影評人
李家驊|影像工作者/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李雪莉 Sherry Lee|《報導者》總編輯
李惠仁|紀錄片導演
林木材|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
林育賢|紀錄片導演
阿茲|視覺文化研究室主編
侯季然|紀錄片導演
柯金源|紀錄片工作者
郭力昕|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兼院長
傅榆|紀錄片工作者、紀錄片導演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聞天祥|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
蔡崇隆|紀錄片導演
王祖鵬|地下電影——
「 紀錄片、劇情片某些時刻並非能明確畫清分界,它時常是模糊的,兩者也的確有其共通性——皆帶著導演『選擇』過後的觀點,在精敲細磨的蒙太奇之中,就藏著人為痕跡。因此關鍵的提問是,何謂虛與實?紀錄片必為真實?劇情片僅有虛假?或許,兩者本該返於『影像』,而影像便勢必反襯時局、映照生活、談論人性。《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一書,藉著縝密的行文邏輯,重新解構、雕塑人們對紀錄片的認識,透過作者時而輕盈、時而嚴肅的筆法,嘗試再次窺探紀錄片的複雜光譜,最後讀者望見的,是創作者們心中堅毅的溫柔鄉。」
影像工作者/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李家驊——
「 對當代世界與影像創作充滿熱情關懷的重要書寫。影像工作者必讀。」
紀錄片導演|李惠仁——
「 除了記錄國家春夏秋冬,書寫社會陰晴圓缺;拍紀錄片的人,總會想『改變點什麼』。」
視覺文化研究室主編|阿茲——
「 紀錄片不只是再現真實的一面鏡子,更是解剖世界的一把利刃,它能輻射出的,是鬆動現實穩定結構的希望與可能。」
紀錄片工作者|柯金源——
「在渾沌的時代,黯淡角落依然看得著亮光!」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兼院長|郭力昕——
「 閱讀全球紀錄片工作者直面現實的不懈努力,能讓我們更勇敢的面對自己與世界。」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管中祥——
「紀錄片雖然未必能改變世界,但卻能紀錄當下,刺激思考;這本書讓我們看紀錄片工作者眼中的當下,以及他們如何反思世界。」
★目錄:
給臺灣讀者的話
前言 何謂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
克里斯‧凱利:「渴望改變的信念, 不會輕易被擊潰」
第一章:
1-1 「主義」把世界淹沒那日
1-2 約書亞‧奧本海默:「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
1-3 卡勒‧拉森:「透過自由表現對抗消費社會」
1-4 鄭潤錫:「噪音無法傳達的語言, 便透過影像翻譯」
1-5 約翰‧伊克曼:「合理使用是深究民主主義本質的證明」
1-6 無國界醫生組織:「提供見證與醫療的前線奮戰」
1-7 紀錄片紀錄片主義的解剖學
-《希望你在這裡》松井至
-《巡警生涯》傑特.雷伊可
-《歌的序章》河合宏樹
-《關於我的自由~SEALDs 2015 ~》西原孝至
第二章:
2-1 將世界連接的命運之船
2-2 原一男:「保持理想, 渴望自由」
2-3 Blackbox Film & Media:「不讓歷史重蹈覆轍,我們有監督之責」
2-4 亞雷希奧‧馬莫:「紀實攝影師是時代的目擊者」
2-5 晉江:「紀錄片是一個愛的過程」
2-6 紀錄片主義的解剖學
-《剛果摔角》內山直樹
-《一個人的福島》中村真夕
-《輪迴情》康世偉
第三章:
3-1 將真實編織成故事,為即將消失的聲音代言
3-2 拉夫.迪亞茲:「我的職責就是製作電影」
3-3 佩德羅.科斯塔:「若無法完整在電影裡呈現他們的故事,等於背叛」
3-4 高山明:「劇場創作不會只有單一類型」
3-5 潔米.米勒:「為遍體麟傷、失去珍惜之物的人帶來勇氣」
3-6 紀錄片主義的解剖學
-《李老師與三十個孩子》米本直樹
-《拉達克:每一個故事》奧間勝也
-《我眼裡的中國》關強
第四章:
4-1 紀錄片改變了什麼?
4-2 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解放觀眾知覺,看見真實與現實的脆弱」
4-3 日本的紀錄片論壇與影展
-Tokyo Docs/天城靱彥
-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藤岡朝子
4-4 世界紀錄片論壇與影展
-Hot Docs/西恩.史密斯( 加拿大)
-IDFA DocLab/卡斯帕.松內( 荷蘭)
- 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林木材( 臺灣)
4-5 紀錄片祭典新實驗: Docu Memento/BUG
4-6 文化雜誌《neoneo》與東京紀錄片影展/金子遊
4-7 SUNNY FILM( 電影發行商)/有田浩介
4-8 紀錄片主義的解剖學
-《Mothers of Change/恐怖分子的母親》竹岡寬俊
-《特許時間的終了》太田信吾
-《東京庫德人》日向史有
茱蒂思.奧斯頓:「多音交響的未來」
結語 紀錄片的夢想仍將持續
<作者簡介>
SOMEONE'S GARDEN
由「津留崎麻子+ 西村大助」成立之公司。從事雜誌、書籍的編輯、設計、app、影像製作、活動舉辦等業務。
著有《世界の、アーティスト・イン・レジデンスから》( ARTISTS IN RESIDENCIES AROUND THE WORLD )( BNN)、編輯設計書籍有《Visual Thinking with TouchDesigner 》( BNN)等。影像編輯有《手芽口土》( Victor)MV、《CLEAR》( Unilever)TVCM、Tower Records《LIVE LIVEFUL》WebCM、《SOCIAL 0.0 LAB》( Motorola Japan)WebCM、《旅旅叨擾》( 旅旅しつれいします)( NHK 綜合頻道)等。參加藝術活動「六本木Art Night 2018」, 並與紀錄片工作者團體BUG 共同打造紀錄片祭典活動Docu Memento。
http://someonesgarden.org
津留崎麻子|日本大學藝術學部評論學科畢業、早稻田大學研究所電影學科修畢。擔任日本Green Image 國際環境映像祭評審委員、東京紀錄片影展單元負責人。學生時期曾在EUROSPACE 工作, 之後曾在Film Center( 現為「國立電影資料館」National Film Archive of Japan)、SPIRAL、UPLINK 從事電影宣傳工作。曾與KENZO 香水合作一項名為
「FLOWER BY YOU」的企劃, 在歐洲各地旅行, 因而結識許多藝術家, 透過《QUOTATION 》雜誌, 介紹海外具有才華的新生代藝術家, 並建立相關網路平臺。
西村大助|以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神經膠細胞的研究取得碩士學位。博士第一年取得藝術家簽證赴美國紐約。每月於CAVE 畫廊舉行展覽會。參與《TOKION 》雜誌創刊, 回日本後負責《TOKION JAPAN 》編輯工作, 曾採訪北野武、是枝裕和、三池崇史、若松孝二、黑澤清、荒木經惟、草間彌生、灰野敬二、內田裕也、黑川紀章、UA、楳圖KAZUO、水木茂、茂木健一郎等人。
譯者:雷鎮興
中日口筆譯工作者。從小就是哈日族,喜愛關注與研究日本的各類文化。踏入譯界後,深感語言、文字帶來的不可思議力量,期盼渺小的自己也能參與其中,盡一分綿薄之力。
譯稿賜教:kaminari1218@gmail.com
★內文試閱:
‧自序
給臺灣讀者的話
大家好,由衷地感謝大家閱讀《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一書。
2018 年,本書在企畫階段時,我們最初選定的採訪地點,正是臺灣──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當時,我們採訪了陪伴抗爭居民一同奮戰、拍攝《柬埔寨之春》的紀錄片導演克里斯.凱利( Chris Kelly);以及為了接觸少數民族文化,勇敢挺進高山地區,完成《上阿甲》的紀錄片導演晉江。我們很榮幸有機會在臺灣採訪這兩位傑出的紀錄片導演。這次,能將本書呈獻給我們採訪旅程中的「第一站:臺灣」,或許正是紀錄片產生的化學效應。
本書出版3 年過後的現在,COVID-19 無情地肆虐全球,人類在各方面遭逢過去不曾經歷過的漫長停滯期。在世界各地,包括紀錄片在內的電影環境,同樣出現了巨大的轉變。在日本政府呼籲民眾自律,盡量避免外出群聚的情況下,不少電影院紛紛受到影響而暫時歇業。目前雖然尚有各種限制,但還是有許多電影院,為了公開上映而持續努力。
儘管面臨嚴峻的考驗,紀錄片工作者們也絕不喪志,他們持續關注著在逆境中必須正視的真實故事。本書介紹的日本紀錄片導演河合宏樹、日向史有、太田信吾,他們在疫情下的艱困處境中,依然努力不懈地工作,希望能夠透過影像,將每一個「聲音」傳達給公眾。最後,他們的作品終於在電影院順利上映。此外,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 播出由導演松井至、內山直樹、久保田徹拍攝製作的紀錄片《東京微弱歌聲》( 東京リトルネロ),記錄生活在東京社會角落的人,在疫情下的內心糾葛、掙扎,以及真實的聲音。而另一部播出的紀錄片,則是內山直樹追蹤一群無家可歸的街友,受到東京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影響,被迫失去容身之處的紀錄短片。這群導演及其作品,正逐漸地受到世界的矚目。
除此之外,我們有緣接下原一男導演《令和一揆》( れいわ一揆)的拍攝工作、日本Green Image 國際環境映像祭( Green Image Film Festival)的評審工作,以及東京紀錄片影展( TDFF)的評審與營運工作。另外,晉江導演也以新作品《一天》參加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我想,這些都是GAME-CHANGING 產生的連鎖效應,而且仍然持續不斷地發酵中。
撰寫這篇序文的同時,此刻我正以線上觀影的方式,參加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本屆榮獲競賽首獎的作品《理大圍城》,忠實記錄示威群眾反對香港《國家安全法》,在香港理工大學展開一場名為「校園攻城戰役」的抗爭運動。導演是一群「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在獲獎後表示:「今後,我們仍然會繼續發起行動,繼續拍攝工作。」我認為,我們也不能停下腳步,除了關注紀錄片中的故事,也應扮演好傳承者的角色,將紀錄片中的每一個真實聲音,盡可能地傳遞出去。
謹此祝福臺灣的朋友和平、健康
SOMEONE'S GARDEN 津留崎麻子2021.10
前言:何謂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
2016 年,一位多年的老友,同時也是紀錄片工作者的竹岡寬俊傳來訊息:「有一群紀錄片的導演夥伴,大家討論想展開一項新計畫,希望你們能一起加入幫忙。」我們當作半開玩笑去聽他怎麼說,結果看到一張空白的東京地圖上,以潦草字跡滿滿寫上「LGBT、前黑道大哥、移民問題⋯⋯」這類新聞播報時罕見的字眼。嗯⋯⋯莫非你打算搞一個像LOFT/PLUS ONE的地方,舉辦現場實況對談活動嗎?我們本做此設想,表達意願想更進一步瞭解計畫內容──若是籌辦活動,筆者西村過去從事《TOKION》編輯工作時期,有主辦談話講座的經驗;而津留崎則參與過EUROSPACE 與UPLINK 這兩間電影公司的電影發行、宣傳工作,我們應該能夠幫得上忙。然而,這群紀錄片導演們聚集在一起,究竟要做什麼事情呢?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們決定去見他們一面。一星期過後,在蕭瑟秋風中,我們前往北品川新馬場車站附近的咖啡館KAIDO books & coffee,參加「BUG」的祕密結社會議。包括松井至與內山直樹為代表的新生代紀錄片導演們齊聚一堂,正熱情地高喊著「紀錄片本應是社會企業家的工作」、「再這樣下去,紀錄片肯定會完蛋」、「真正足以傳達理念的場域根本不夠」的交談聲此起彼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日本居然還存在著如此充滿傻勁而有趣的一群人⋯⋯」這是我們見到他們後的第一印象。
於是,在認識這群人之後,我們經常見面,討論紀錄片的想法,時間長達半年以上。我們一起製作了一部以旅人為主題的NHK 紀錄片《旅旅叨擾》( 旅旅しつれいします),拍攝賭上人生而踏上旅途的人物故事。歷經許多迂迴曲折的過程後,我們更打造出全新型態的紀錄片祭典活動「Docu Memento」。另一方面,每當與從事紀錄片工作的他們認真探討紀錄片時,總會有一些疑問湧上心頭。比方說「究其根源,到底什麼是『紀錄片』?」「只是乏味無趣的影像紀錄嗎?」「拍攝一個人死命大口吃著麥當勞?還是手持GoPro 追著鳥類拍攝?或節目片尾出現鯨魚徜徉大海的感動畫面?」「網路影片也算紀錄片嗎?」「導演偶爾在畫面中露臉,這類很有真實感的作品如何?」「安排演員入鏡也算紀錄片嗎?」等各種想法。
接著我們想到了兩件事:
一、到底是什麼原因,推動著這群充滿人情味的紀錄片導演們?
二、「努力記錄眼前現實情況的紀錄片,其中必然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的假設是否為真?
於是,我們以極具企圖心的「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概念作為書的核心,啟動《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出版計畫之旅,採訪了30 位以上的紀錄片導演與相關工作人士。
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是我們自行創造的詞彙。以企業大膽祭出策略時,經常使用的「Game-changing」這個詞做形容,另外我們結合紀錄片近百年歷史中,只出現過數次的「Documentarism」這個字,嘗試能否再次定義紀錄片,從中捕捉全新意義。然而,幾乎每天出現在電視上,令人習以為常的紀錄片,我們為什麼要以全新的語言再次定義它呢?因為我們深信,紀錄片中暗藏著Game-changing 的可能性。此時此刻,假新聞滿天飛,有許多人認為,每過一秒,世界就距離毁滅更近一步。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了解紀錄片中每一個觀點建構的真實,它能震撼觀看者的心靈,為人們與社會帶來「改變」,相信從這群紀錄片導演展現出的態度,我們能學習到更多重要的事物。
本書中,我們將詳細介紹這些特別挑選出的人物與作品。這個時代,由於網路收看與自媒體的普及,紀錄片的發展越來越蓬勃,越來越趨向多元化。本書將從各個角度介紹紀錄片產業,期盼讀者能夠了解紀錄片的「改變力量」以及重要精神,這是我們最大的心願。
SOMEONE'S GARDEN
津留崎麻子、西村大助
‧摘文
1-2 約書亞‧奧本海默:「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
30年前,印尼發生一場名為「清洗共產黨」的大屠殺事件。美國紀錄片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發現這場悲劇並非過去式,它仍存於現在的此時此刻。導演在紀錄片中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實驗,他安排以殺人事蹟為榮的加害者,與每天恐懼被屠殺者包圍的受害者見面,讓彼此面對面接觸。奧本海默導演拍了兩部作品,帶給世人極大震撼。其中一部是讓過去參與大屠殺的兇手,再次詮釋自己的作品《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另一部是親哥哥遭到屠殺的弟弟,對加害者提出質問的作品《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奧本海默導演到底是如何拍攝出這兩部奇蹟般的作品呢?
●世界充滿各種暗號。接下來,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就好
Q:聽說之所以想揭露這段大屠殺的歷史,來自於2004年在印尼蛇河沿岸採訪兩位加害者時所獲的靈感?
Joshua Oppenheimer( 以下稱為JO):這群當時參與大屠殺的人,誇耀往事的身影中,有一種令人無法言喻的毛骨悚然。我察覺到,他們並非單純想出名或瘋狂才願意站在鏡頭前,而是「社會本身」處於一種瘋狂狀態。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告訴世人事情的真相。2003 年開始,我與《沉默一瞬》的主角阿迪成為好朋友。最初透過他的親戚,我與兩位加害者見面,接著又認識其他加害者,陸陸續續展開拍攝工作。這群男人驕傲談論著大屠殺的點滴回憶,但是生活在他們的陰影下,是何其恐怖的一件事啊。拍攝他們的某個夜晚,我腦海中閃過了兩個念頭。其中一個念頭是,他們為何能如此自豪談論這些往事?每當他們驕傲地高談闊論時,總是有一個傾聽的對象。也就是說,他們正在對著某個人炫耀這些事情吧?他們期望對方怎麼看待他們?包括他們的兒女、兒孫女,還有我,以及世人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如何看待這樣的自己?假如讓他們試著詮釋本來的自己,就能以虛構的方式拍攝紀錄片了。我的疑問是,隱藏在他們背後的到底是什麼?他們是否曾想過贖罪的問題?我決定用一種方式去質問他們,那就是透過「重演」,讓他們思考這些事情的本質,最後才完成了這一部作品《殺人一舉》。另外,還有一個念頭,家人慘遭屠殺的遺族,數十年來卻與這群加害者生活在同一個地方,這到底又是什麼狀況呢?加害者依然擁有權力、威脅著人們,談起過去的罪行時,總認為是一種榮耀。然而存活下來的人,卻靜靜地生活在語言之外的沉默黑暗裡。這些沉默,在他們的家人、身體、記憶之中,產生了什麼作用?又留下了些什麼?這些疑問,全部都放在第二部作品《沉默一瞬》。
●重現屠殺的場景,喚醒罪惡的記憶
Q:你如何讓這些屠殺者重演當年的屠殺場面?
JO:《殺人一舉》的主角安華.剛果,是我在2005年拍攝的第41名加害者。2004年1月,我在蛇河採訪完最初的兩名加害者後,想儘量找到更多加害者。然而這些加害者全都如出一轍,談起自己手染鮮血的殺戮事蹟,個個引以為傲。我想要了解他們是否在乎其他人眼光,於是提議:「你們參與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事件。為了社會與你們自己,你們願意讓大家看見你們真實呈現的自我嗎?」因此,我請他們帶我回到實際發生大屠殺的現場,希望他們重現當年的殺人經過。接著,我又再度向他們提議:「請這樣繼續下去。請告訴我,你們用什麼方法讓雙手沾滿鮮血呢?希望你們透過戲劇的方式重演一次,讓我拍下這些過程。同時,我也會把你們『想給大家看什麼、不想給大家看什麼』的討論拍下來收錄在影片裡。」然而仔細想想,我並不清楚他們為什麼連「不想給大家看什麼的討論過程」也都同意我拍下來。所以,除了他們提出想要刪掉某段情節的發言可以拍,甚至連拍下他們討論這些事情的經過也沒關係。他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對此感到疑慮。我向他們說明,我會把他們重現殺人現場的戲劇情節,與他們討論如何詮釋的過程,穿插組合在一起,這將會誕生一部前所未見的新電影;透過這部紀錄片,他們或社會的疑問,相信一定能夠找到答案。首先,我向主角安華提出想法。安華與我之前拍過的40個人截然不同,他無法隱藏內心的痛苦。我們見面的第一天,他帶我去一棟屠殺現場的大樓屋頂,當場示範如何用鐵絲把對方的脖子勒斃,講完之後卻突然跳起恰恰舞步。紀錄片中,有一個片段是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刻。我去他家拜訪,徵詢他拍紀錄片的意願,雖然很有可能遭到拒絕,但我還是按照自己的習慣,扛著攝影機前往拜訪。到了之後,安華說:「聊聊天無所謂,但是我的太太目前有訪客。」於是帶著我轉往頂樓去。接著我察覺到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已經40年沒爬樓梯的安華,一到了屋頂,立刻發出痛苦般的「嘆息」。原來這個地方喚醒了他曾經在頂樓殺人的痛苦回憶,不經意地將內心「感受」顯露出來。「或許我想了太多以前殺人的事情。為了不讓自己瘋掉,我盡情地活在酒精、嗑藥與跳舞的生活時光。你看,我的舞跳得還不賴吧。」這一定是為了忘掉痛苦才跳的舞,我拍下這一幕,內心暗忖,一定要將他的真實內心告訴世人。就像映照出自己的鏡子一樣,希望安華也能夠好好檢視自己。但同時我也擔心,在電影院分享這些拍攝過程的相關風險。畢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嘗試過這樣的挑戰,大家都認為它過於危險。「怎麼把我拍成這個樣子,簡直太過分了!我要立刻退出演出。」我想安華說出這些話的可能性相當高。因為第一次看《殺人一舉》,安華在確認自己的表現時,就曾說過:「衣服不對,簡直像要去野餐一樣!」如果他又看到影片中自己困惑的神情時,會不會說:「夠了!怎麼把我的臉拍得這麼糟?我才不想拍這種鬼東西!」隨即叫警察或(準軍事組織)班查西拉青年團的人傷害我們。在這過程中,我捏了好幾把冷汗。我甚至事前安排好攝影團隊去機場待命,要是有個萬一,隨時可以逃往國外。假如我的手機沒送出「沒問題」的訊息暗號,就等於終止拍攝。雖然安華覺得這一場戲不太對勁,但卻一直以「服裝不對」之類的理由,掩蓋自己殺人行為的「錯誤」。這是因為他不斷說服自己,從1965 年開始到結束那一刻,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正確的;但對他來說,看到影片中的自己,卻是初次體驗,所以他在當下選擇欺騙自己,以及拍攝這一切的我。我認為他之所以感到「不對勁」,正是因為他的良心發出了「這裡很奇怪喔!」的聲音。然而安華又說:「把劇本重寫一遍,讓我換上另一套衣服。還有,演員和場地都換掉,這樣才能繼續拍下去。」我們表示同意,接著進行下一場拍攝。但接下來是更殘暴的場景,他分別扮演拷問共產黨員以及被拷問者的角色。然而每一場戲在拍攝進行時,他都感到罪惡而痛苦不已。為了揮去自己心中產生的疑惑,他多次要求暫停拍攝,改拍其他不同場景的戲。事實上,我們的拍攝方式,包括所有的場景、劇情,全都交由安華自行設計安排,因此在不知不覺中,這部電影就成為一部極具分量的作品了。
Q:最後安華有如此大的轉變,是因為與導演的對話而產生改變嗎?
JO:不只是和我對話,由於安華也扮演被拷問的犧牲者,所以心境上才會出現轉變。事實上,從我們第一次見面開始,我就發現他時常會扮演犧牲者。好比在跳恰恰舞的大樓屋頂上,他向我示範遭到屠殺的受害者如何被鐵絲勒死,然而他卻感覺罪惡痛苦,內心充滿矛盾糾結,才隱藏了那一瞬間的真實自己。他為每一個加害者所犯下的罪行感到痛苦,為了想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這些加害者不斷地向人們誇耀自己的能力,彷彿自己才是正確歷史的勝利者。他們自豪地告訴我們曾經喝下了受害者的血,以及如何將敵人開膛剖肚,所有作為都是英雄義舉,只為剷除共產主義的威脅。安華最後出現改變,或許真的是來自於我們的對話,但事實上,從安華到產生疑惑、行為上出現抗拒,我們一起度過了5年的拍攝時光。我拍攝2 至4 個月後回丹麥一趟,過3至6個月後再回印尼繼續拍攝工作,如此周而復始。
Q:導演在電影拍攝中會說印尼吧?
JO:對。印尼話並不是太難學的語言,我覺得日語比較困難吧。目前正在拍攝的電影需要使用格陵蘭島方語,我也覺得非常困難。雖然我與20年前邂逅的日本伴侶生活在一起,但現在仍然不會說日語。我希望有一天能在日本邊拍電影邊學日語,這才是我的最佳學習方法。終結不了的暴力與深植內心的恐懼壓迫。
Q:你是如何得知1965年發生的印尼大屠殺事件呢?
JO:2001年,我接受邀請前往印尼一處種植園的村落,進行電影製作研習營。當年我27歲。這座村落正是《沉默一瞬》主角阿迪的故鄉。過去一直嚴禁成立工會的蘇哈托獨裁政權瓦解過後3年,村民為成立工會紛爭不斷,因此我主要目的是拍攝他們。儘管蘇哈托獨裁政權瓦解,實際上成立工會依然困難重重,經常會上演各種鎮壓與暴力事件,因此有人提議,何不拍攝一部「為成立工會而奮戰到底的電影」。當時,由於他們沒有製作電影長片的經驗,所以這項計畫就在大家邊學邊拍之下進行。大家每天拍攝結束後,會聚集在庭院中播放,如此周而復始。當我到這裡後,得知他們非常擔心一個問題,許多女性勞工罹患肝臟疾病,很多人在45歲之後死亡。主要原因是殺蟲劑含有劇毒,每個人在工作時並沒有穿戴面罩與防護衣物。因此,工會最初的訴求,就是要求提供保護身體的防護衣物。他們的雇主是一間比利時的企業,雖然知道工會訴求,卻完全置之不理,還聘僱參與大屠殺而惡名昭彰的班查西拉青年團成員,以暴力行為讓工會成員閉嘴,結果這些勞工最後取消了要求。我實在無法理解其中原因,於是問:「沒有防護衣物這件事攸關性命,為什麼不繼續爭取?」他們回答:「1965年發生的大屠殺事件,班查西拉青年團在當時殺了很多人。我們的家人根本不是共產黨員,只是因為工會成員身分就慘遭殺害。」如今這些加害者手上仍然握有大權,大家害怕同樣的事情會再度降臨到自己身上。進一步了解的過程中,我發現大家擔心失去性命,不只是因為女性勞工受到殺蟲劑毒害,還有活在威權下的「恐懼」。當時只要一提到1965年的大屠殺,大家就會害怕,沒有人敢碰觸這個話題。後來過了一段時間,因為他們的期望,也為了再拍一部與他們有關的電影,我又再度回到印尼。
●紀錄片帶來了
Q:改變我感受到你的作品影像美得如詩如畫,其中傳遞出的訊息更是出色。
JO:人只要看著影像、聆聽聲音,就能夠產生某種特別的感覺。只要連結這些感覺,就能夠創造某些事物。我正是以這種心境開始製作影像。雖然我不是記者,也不曾受過紀錄片的專業訓練,但我非常努力製作紀錄片,希望觀眾能夠沉浸其中。因此,我嘗試尋找其中的動人旋律。《古蘭經》中有一章節記載:「世界充滿各種暗號。接下來,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就好。」拍攝過程我總會想到這一句話。特別是執行紀錄片時,我經常會試著解開藏在影像中某些意義深遠的暗號。比方說,一道光線、蟋蟀的叫聲⋯⋯等; 到了夜晚,彷彿亡者之靈出現般的氣息、穿著女性粉紅禮服的赫爾曼,以及巨大魚類的物體。這些影像中,隱藏著整個故事的寓意,它能抓住觀眾的情緒。透過電影中傳達的真實,往往能使觀眾茅塞頓開。因此,我身為影像創作者,最喜歡的一件事情就是拍攝製作電影。
Q:你的第一部電影長片為什麼會選擇以紀錄片的方式拍攝呢?
JO: 首先,所有偉大的紀錄片作品,一定都具有「產生改變」的力量。有許多人到現在仍然誤解,以為紀錄片就是紀錄世界的影片。如果我們去看優秀的紀錄片作品,就會發現許多作品都是紀錄片導演與拍攝對象的合作關係。他們介入世界,找出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打造出過去不曾發現的新狀況。讓大家看見原本看不見的事物,把所有人的視野引領到新的地平線,即便那不是一個會讓所有人感到舒適愉快的地方。就某種意義來說,它或許與治療有些相似。好比你在一間安全的房間裡安穩地坐著,只有感覺朝向不安全的場域擴散。拍一部紀錄片也是同樣的道理,它能夠創造出全新的真實感覺。但並非記錄「真實」,而是創造「全新的真實」。這種真實感覺並不是只有你個人才能擁有,它是與其他人共同擁有的真實感覺。它與「演戲」是完全不同的。所謂演技,只能按照寫好的劇本詮釋,在劇本的指示下創造情境。但紀錄片不同,紀錄片在被攝者發生變化時,也會促使觀眾產生變化,同時也會為世界帶來改變。或許紀錄片與虛構創作有相似之處,但紀錄片的素材本身隱藏著祕密,它必然會產生不同於虛構創作的共鳴。好比觀眾透過紀錄片可以得知「此刻眼前的這些人正處於變化的情況當中」。拍成紀錄片之後,這些沒有受到正視的事實,以及伴隨著痛苦的真相,將會透過紀錄片被大家清楚看見。因此,製作一部紀錄片作品,有時候會充滿美麗,有時候卻也充滿危險。
你的作品帶給世界極大震撼,在
Q:籌備期間時,曾想過它會產生如此驚人的現象嗎?
JO: 我沒有想過會造成熱烈的迴響。當我參加首映會與頒獎典禮,表達內心感動時,仍有一種無法置信的感覺。那是無法令人忘記的重要時刻,同時我也由衷感激電影中許多匿名參加的協助者。我並沒有將這些作品視為「紀錄片」,因為「紀錄片」的定義範圍實在太狹隘。或許這句話聽起來有些傲慢,但我並沒有貶低它的意思。如果與佛雷德里克.懷斯曼( Frederick Wiseman)等優秀的前輩比較,我的作品數量根本無法與其匹敵。儘管如此,我仍然嘗試了新的表現手法,包括以虛構創作以及紀錄片等形式。雖然這兩部作品的製作方式完全不同,但它們就像鏡子的表與裡一樣,兩部作品是同一個世界,它們有各自互補的地方。
Q:過去你曾說過「並不想創造英雄」,不過《沉默一瞬》中,阿迪的表現確實相當勇敢。
JO: 我也是這麼認為,這意味著阿迪值得「讚賞」。因為我極力排除感傷主義。為什麼阿迪在紀錄片中要如此頑強地探究下去?我在開拍之前,經常問他的家人:「這樣拍下去確定沒問題嗎?」儘管家人反對,阿迪仍然持續前進,沒有任何一點遲疑。沒有人是完美的,加害者的後代或許以後也會成為加害者。但相對的,他們也有可能成為受害者,就像被安華或他的同夥處決掉的家人後代一樣。多數紀錄片就像電影《星際大戰》清楚地描繪出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但是我認為這並不正確。安華以加害者的身分自豪地高談闊論,在他的每一句話中,我們都能感覺到罪惡意識。他們之所以感到罪惡,正是因為其中有道德的存在。
Q:我們可以在紀錄片中看到加害者自稱為Preman
JO:印尼語「Preman」(流氓、自由人)的語源來自英語中的「FreeMan」,代表自由人。但非常諷刺的是,這起發生於印尼的大屠殺事件,事實上有西方國家撐腰,甚至還有人作證,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也運用私人資金,提供這群殺手集團班查西拉青年團。日本舉行的首映會上,我也從印尼前總統蘇卡諾(Soakarno) 的遺孀黛薇夫人(Dewi Sukarno)的口中證實了這一點。西方國家與日本以「自由民主」之名,竟然金援殺人機器,成為大屠殺事件的幫兇。我原本要把紀錄片的標題命名為「Free Man」,但在韋納.荷索( Werner Herzog)的建議下,最後才變更為《The Act of Killing》。若你問我為何會想取名Free Man,是因為出色的電影名稱能挑起觀眾的想像力。對看過紀錄片的人來說,Free Man 的命名或許感覺也不錯,但我認為《The Act of Killing》更能激起觀影的興趣。
Q:我非常喜歡電影中片尾這首〈生而自由〉(Born free)曲子
JO: 安華也很喜歡這首歌曲,這首曲子總能把他的思緒帶往「自由」境地。藉由安華主張他們這群人的自由,才能承認自己犯下的罪惡。儘管沒有其他選項,他們仍堅持自己是「自由的」。這裡產生了一個關於人類自由的哲學提問。這首曲子原本是電影《獅子與我》( Born free)的主題曲,我們絕對不能忽視這項事實。我原本想諷刺美國文化造成的影響,然而卻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它拋出了更深一層的問題。一整排動物標本的畫面搭配〈生而自由〉這首歌,加害者一起通過動物標本下方的門,彷彿讓人窺見參與屠殺的司令官生活。在最後犧牲者向屠殺者致謝的場景中,這首〈生而自由〉聽起來就像西方文化的國歌一樣,我們瞥見了安華渴求自由的神情。
Q:紀錄片中使用了好幾次「Sadism」這個字吧?
JO: 我用這個字並不是要他們向自己的罪行道歉,而是要讓他們正視自己受到良心苛責所隱藏的痛苦。我一直讓安華重複觀看影片中的自己,他的情緒越來越難受,我在這時使用這個字則有「你的樣子真狼狽啊」的意思。在印尼,這個字簡稱為「Sadi」,它具有雙關語義; 其中一義是「帥、酷」,另一義則是「暴力」。過去,印尼的恐怖電影經常會使用「Sadi」這個字。
●當影像成為鏡子一定能夠傳達新的訊息
Q:你認為紀錄片與藝術能夠改變世界嗎?
JO: 我認為可以,因為高明的藝術形同一面鏡子。現實上,將尚未發掘的震撼故事傳達給大眾是新聞界的工作,它就像一道光束照向黑暗,為大眾開啟一扇看見未知的窗。而藝術或紀錄片發揮「鏡子」作用時,能使人產生強烈感受,進而接收全新訊息。「鏡子」能反映出我們自身,強迫我們凝視難以忍受的真實樣貌,儘管其中存在著難以認同的事物。但我們若能正視它,就能解決未知或棘手的問題,進而出現改變。我認為《殺人一舉》與《沉默一瞬》這兩部作品是強烈反映印尼社會的一扇「窗」,同時也是映照出我們自身的一面「鏡子」。倘若這兩部作品能夠為印尼帶來改變,我認為正是因為它成為了印尼社會的一面「鏡子」。如今,已有數千萬以上的印尼人看過我的作品。接著,他們開始對國家產生新的體認,思考該如何面對過去發生的歷史。除了過去與現在,包括目前的政府,軍隊擁有的權力、不義與腐敗,大家已開始去思考這些問題。讓他們改變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作品拍出他們不曾看過的印尼,而是作品成為了一面「鏡子」。就像童話繪本《國王的新衣》中,小男孩發揮了改變的力量。小男孩毫不猶豫地說:「為什麼國王沒有穿衣服呢?」人民才驚覺國王裸體,而人民太過恐懼,沒有人敢開口指出這項事實。然而,小男孩卻以無法否定的方式直接講出來,人民因此感到羞愧、不知所措,懊惱受到恐懼束縛而無能為力的自己。在那過後,人民下定決心,誓言絕對不再屈服內心的恐懼。一定要開口說出國王裸體的事實,就像開口說出印尼曾經發生的大屠殺事件,是一項極為深重的罪惡。然而,何時拿出「鏡子」?選擇適當的時機則相當重要。前面曾問到「在籌備拍紀錄片時,有想過它會受到讚譽嗎?」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沒有」。我花了非常長的時間投入這部電影,實際上花了11 年到12 年左右。剛開始到村落時,我還沒有行動電話。但經過幾年後,村民人手一支手機,甚至還有臉書帳號。「既然印尼都轉變了,我還要繼續在原地打轉嗎?」我決心完成這部作品。當這部紀錄片在世界各地上映,印尼新世代的孩子已長大成人,參與屠殺的人也從軍隊第一線退了下來。正確而言,由於時光流逝,過去的加害者看了紀錄片,終於能去談論這段往事。這代表強而有力的藝術作品,對過去無法動彈的人們,發揮了改變的作用。儘管,就算再怎麼優異的作品,也未必能帶來政治上的轉變。韋納.荷索在看過我的紀錄片後卻說:「藝術無法改變什麼。但是這一部作品卻產生了改變。」
●感同身受的心
Q:拍完這兩部紀錄片,你本身出現了什麼改變?
JO:我變得更有自信了,因為過去我沒有製作過電影長片的經驗。這些存活的受害者希望我拍一部加害者犯下屠殺罪行的電影,起初我還以為會遇到什麼可怕的怪物。然而,實際上我見到的都是「人」,所以心裡鬆了一口氣。我開始思考,既然大家都是「人」,就一定能找出一條路,避免再犯下相同過錯。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化學家普里莫.萊維( Primo Levi)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上雖然有怪物,真正的危險卻幾乎不存在。相較之下,更危險的地方,是人民毫不懷疑的盲目行為。」我內心一直牢記這句話。我從小就是個心思細膩、感受性強的孩子。還記得有一次,我在山上抓到一隻青蛙,很想要把牠帶回家,但心中不禁思考:「還是放回原地好了,不然牠一定會迷路的。回去吧!」接著就轉身往回走了。至今我依然無法打死蚊子,捕捉之後會往室外放。或許有人會覺得奇怪,但我對自己有一顆「感同身受的心」極具自信。我與參與屠殺的安華等人變得要好,不少朋友對此擔憂。然而,無論做過多麼過分的事情,我們對他們必須敞開胸懷,其中也必然包括了忍耐。
●未來展望
Q:你打算繼續拍攝印尼的後續發展嗎?
JO:我這兩部作品是我以印尼為主題的完結作品。我再也無法回到印尼,因為印尼政府限制我不得入境,目前形同從軍隊的威脅下逃出來一樣。前陣子,9月30日紀念大屠殺的這一天,軍隊最高長官向軍隊下令,警告不得讓《殺人一舉》公開上映。因此,我現在應該也無法安然回到印尼吧。與我共同完成作品的朋友就像家人一樣,一想到再也無法回到印尼就悲從中來。如果能回去,或許就能再繼續拍攝下去。同時我也思考,第1 部作品完成的使命,就是讓印尼人明白,1965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它把腐敗、恐怖與不義的恐怖連鎖完全攤在陽光下;第2部作品則成為輔助角色,它告訴大家明白真相後,必須從正義走向和解,這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接下來的電影續集不該由我來製作,應該由全體印尼人民一同撰寫下去; 大家接續的「未來」正是第3章。我也許無法馬上作答,不過我目前正在拍攝一部名為《The End》的電影。這部電影描寫生活優渥的一個美國家庭,故事的時空背景是世界末日過後的20年,一家人與3 名管家一起生活,即使世界毁滅、地球走向殞落,他們仍然保持樂觀,活在過去的榮耀、社會地位,以及堅信人性未泯的妄想執著。目前在籌備階段,我打算2020 年開始拍攝。順帶一提,虛構電影最大的優點,就是攝影工作不需要花5 年的時間
(笑)。
(2018年9月,Skype採訪)
約書亞.奧本海默 Joshua Oppenheimer
出生於德國系猶太人的家庭。雙親在其年幼時因納粹展開猶太人大屠殺失去家人, 拚命
從德國逃往美國。在哈佛大學與倫敦藝術大學學習電影製作。2012 年, 發表首部長片
紀錄片電影作品《殺人一舉》, 透過加害者的觀點, 描述印尼發生軍事政變的大屠殺事
件, 並入圍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獎。2014 年, 再度以前作中的事件為主題,
發表以受害者觀點來敘事的續篇作品《沉默一瞬》, 並榮獲第71 屆威尼斯國際影展評審
團大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 FIPRESCI Prize)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