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書,我與文學的美好初識/張士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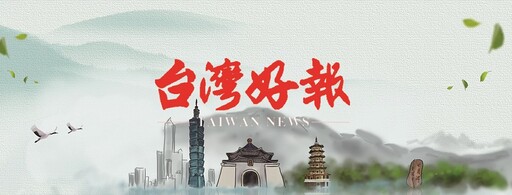
張士傑
在我幼小的心靈深處,有一個特別的角落,那裏珍藏著與小人書相關的溫暖記憶。那個家貧如洗的年代,父母辛勤勞作的身影背後,是買不起一本小人書的無奈。鄰家孩子手中的連環畫,常常讓我如饑鼠窺廚,饞涎欲滴。小人書成了我心中最閃耀的星星。
記得那時我上小學二年級,在二舅家看到在甘肅酒泉當兵的舅舅寄來家信,仿佛昭示看小人書機遇到了。第二天,我悄悄給舅舅寫了封信,說我要看小人書。當我把信交給老師讓她幫助寄發時,老師笑著說:“你這信封上寫的格式是對的,但收件人後面括弧內備註的稱呼‘赳赳’是錯別字。”在老師的指導下我把“赳赳”改為“舅舅”。或許,那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兩個字裏暗含著多少童真和渴望。
兩個月過去了,在我失望之時,卻收到來自北京的小包裹,原來是舅舅從酒泉調到北京部隊了。打開它,瞬間,一本本小人書躍入眼簾。那些栩栩如生的插圖如春風般溫暖著我的心靈,讓我頓時忘卻了生活中的瑣事煩憂。
這些小人書很快成為我最忠實的心靈夥伴。每當遭遇不快,翻開《哪吒鬧海》看小英雄大鬧龍宮,或是《白蛇傳》裏白素貞盜仙草的執著,或是《三國演義》裏關雲長單刀赴會的凜然,或是《西遊記》中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恣肆,總能讓我破涕為笑。夜裏入夢,常是“三英戰呂布”的刀光劍影,或是“黛玉葬花”的淒清畫面。那些方寸之間的悲歡離合,在我心中悄然種下了文學的種子。
奇妙的是,這些圖文並茂的小冊子不僅豐富了我的想像力,更讓我的作文水準突飛猛進。老師開始將我的文章當作範文誦讀,同學們投來豔羨的目光。這讓我充滿成就感,也讓我更加堅定了追逐文學夢想的決心。小人書帶來的不僅僅是文學啟蒙,它還如同一扇窗,讓我看到了更廣闊的人生舞臺。
再後來舅舅寄來的書籍從《東周列國志》《聊齋志異》等連環畫,逐漸升級為《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最後竟有《水滸》《三國》之類的大部頭。他復員回鄉時,行李箱中大半都是給我買的書籍。
梁曉聲先生說過:“小人書是我能咀嚼文學之前的‘代乳品’。”此言道出了多少人在文學道路上的心聲。正是這小小的一本本手冊,把文字之美傳遞給我們,讓我們勇敢地去探索更廣闊的人生。
隨著歲月流逝,我漸漸長大,開始嘗試用文字講述自己的故事。在漫長而富有挑戰性的寫作旅程中,我依然會不時回頭望向那一段柔軟又美好的時期。如今,我的作品散見各種媒體400餘篇首,被隆堯縣政協聘為文史專員,榮獲“隆堯縣文化名家”稱號,有幸的是,最近又加入了《小散文》雜誌作家理事會行列。這些成就背後,都離不開曾經那個懵懂卻執著的小孩對小人書無盡熱愛的滋養。
而更令我欣慰的是,我的作品集《啟航》即將出版,這是對那段與小人書相伴歲月的最好致敬。每當提筆,眼前仍會浮現兒時那些小人書的畫面——這些畫面早已融入血脈,化作我筆下的墨痕。
前日整理舊物,偶然翻出一本殘破的《西遊記》連環畫,頁角已經捲曲,封面也褪了色。我輕輕撫摸著它,忽然看到舅舅當年在扉頁寫給我的題字:“書是糧食,不是裝飾,好好學習,吃透它。”
如今糧食已化為血肉,而那個趴在炕頭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孩子,也長成了寫書人。拙作《啟航》的扉頁上,我特意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獻給那些曾經滋養我心靈的小人書,和那個在貧瘠歲月裏為我播撒文學種子的舅舅。”
那些小人書不僅是一種閱讀方式,更是一段段珍貴的人生經歷,是啟蒙理想與追求初心的重要源泉。我的作品集《啟航》的出版,正是我對自己文學啟蒙之路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對那些滋養過我的小人書的最好報答。
- 記者:好報 編輯
- 更多生活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