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鵲在誰家簷下牽掛/王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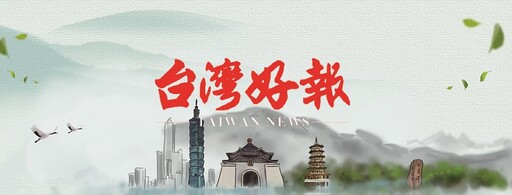
王涵
七月初七,天剛破曉,父親在巷口那青石板旁。身旁竹筐裏蜷縮著兩只灰濛濛的喜鵲,好似剛長途跋涉完一般,羽毛沾上了露珠。他用煙袋鍋輕輕點了點它們的小腦袋,不知想到了什麼,低聲笑了起來。
《詩經》中“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這是先民對天象發出的第一聲驚歎;漢魏之後,牛郎織女被分隔於銀河兩岸,喜鵲一夜之間搭起橋樑,將思念轉化成一年一會的儀式。
唐宋時期七夕是穿針樓上的女兒節,乞巧、望月、曬書,把女子的才情與心願融入月色之中。到了明清,巧果、磨喝樂、水上浮針,市井煙火讓銀河來到灶台與燈市之間。昨夜,城市樓宇的燈帶顯示出“七夕快樂”,外賣小哥摩托尾燈在雨中連成一條紅色天河;而在千裏之外的鄉村,父親的竹筐依舊空空——喜鵲早已飛進城市送快遞了。同一顆星,同一根羽毛,古今之間,七夕的故事被重新書寫。
神話沒有褪色,只是換了人間背景。
七夕或許在商業霓虹下,玫瑰、巧克力和直播帶貨,把鵲橋變成物流鏈上的訂單編號。商場大屏滾動著“限時秒殺”,快遞小哥的保溫箱裏裝著和數字“九”有關數量的玫瑰,宛如一座移動花園。直播間裏喊“上鏈接”,男孩在螢幕外掐點付款,只為給心愛的女孩一個驚喜,此刻,愛情被壓縮為“秒殺成功”的提示音。
七夕在生活場景裏,父親進城扛著大包,肩膀上的勒痕似一道道舊年的鵲橋。母親在家熬夜烙巧果,灶台油煙把月色熏得泛黃。年輕人加班到十點,在便利店點一份外賣巧果,塑膠盒上的水珠滴在報表上,如同一場袖珍雨。他們都在為學費、房貸、明天搭建橋樑——銀河不在天上,而在一張張未還清的帳單裏,人們努力生活,為家人們架起一座座鵲橋。
七夕在我們純粹的情感間,地鐵末班車上,女孩把耳機分一半給男孩,共用歌單裏藏著不敢說出口的名字;鄉村視頻號裏,老兵用粗糙的手給老伴戴上自己打磨的木梳,木齒劃過銀髮,幾十年溫柔在此刻體現。橋不再是一年一會,而是“日日相見”。通過掃碼、高鐵、視頻通話等現代聯絡方式,把“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譯成“我下班了,馬上到哦”。
於是,七夕的意義脫離書本,進入生活當中,被重新詮釋。把銀河詮釋成距離,喜鵲就是所有替我們負重前行的人。把“一年一會”詮釋成“朝夕相伴”,橋也不再是木石,而是信號塔、鐵軌、快遞櫃。把“乞巧”詮釋成“求自立”,女子不再只求手巧,更求心巧事巧業巧,她們在寫字樓敲代碼、在實驗室調試劑,把七襄的織機換成鍵盤與工作臺。
銀河哪里在天上?它藏在巧果的焦香裏,在喜鵲濕漉漉的翅膀上,更在父母無聲的思念裏。
“天上的橋一年搭一次,人間的橋啊,得天天搭著才穩固。”
今夜,如果你正巧路過天橋,看見車燈匯成一條流動銀河,請記住:每一盞尾燈裏,都有一只小小的喜鵲;每一張回家的面孔,都是正在渡河的牛郎織女。天上的橋一年搭一次,人間的橋,只要肩上有擔子、心裏牽掛誰,就得天天搭、日日穩。
於是,七夕不再是遙遠的星辰傳說,而是我們共同撐起的日常煙火。抬頭,是亙古不變的星斗;低頭,是萬古常新的炊煙。喜鵲在哪戶人家簷下歇腳?它歇在每一盞不熄滅的燈裏,歇在每一雙被生活磨出繭子的手上,歇在每一次掃碼、每一次擁抱、每次加班後仍亮著的窗口。
銀河從未遠去,它只是化為了人間燈火,等著我們抬頭,也等著我們回家。
- 記者:好報 編輯
- 更多生活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