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雙手/付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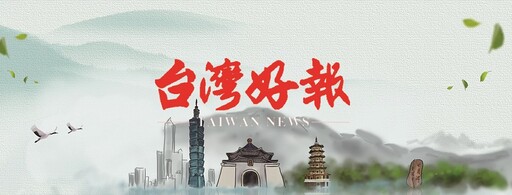
付令
時光匆匆,歲月的長河中流淌著無數記憶片段,而我最難忘懷的,便是記憶中那雙溫暖而有力的手。那雙手,曾是我幼小心靈中最堅實的依靠,是我成長道路上最明亮的指引。
記得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季,父親領我到廠裏的照相館,那是兩歲的我第一次站在鏡頭前,緊張又好奇。攝影師定格了我和充氣長頸鹿的合影。
記憶中,年輕的父親,雙手寬厚而靈巧。作為一線產業工人,工廠繁重的軍品生產任務使他養成了良好的工作技能,熟練地使用鉗子、扳手完成產品裝配。雖是知青,沒能讀大學,但他仍富有想像力,很多材料在他手上變成了一件件工藝品:單位上繪有精美圖案的木盒、接線板,還有常用的工具。
記憶中,年青的父親,依靠雙手帶來很多驚喜。記得家裏第一臺黑白電視機是父親組裝的。那段時間,總見他用電烙鐵線上路板上焊接元件。一天深夜,幼年的我醒來,看見那個神奇盒子的螢幕上顯現出方塊底板的圓圈圖案,圓圈還不太圓。我驚呼:“桃子!”三十歲出頭的父親笑了,經過一番調試,那個圈圈就已經很圓很圓,周圍的方格子也很正。他告訴我:“這是電視信號測試圖。以後咱家就有電視看了!”
因為興趣愛好和專業特長,在廠裏小有名氣的他從車間、設計所,一路調到工會工作。那時工會為了豐富職工業餘文化生活,開始搭建閉路電視、衛星電視接收站。父親與建設方通力合作,圓滿完成了任務,職工和家屬們拍手稱讚。九十年代中期,宣傳部組建電視中心,制播一體化,他再次調動到了宣傳部。
在人生道路的轉捩點,都有父親凝練的投影。那年初秋,我參加高考被飛行學院錄取。四十多歲的父親為遠行的我準備行裝。他的臉上洋溢著笑容,在百貨商店買了一口組合式瓷缸交到我手上說,未來要靠你自己,飯碗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時的我卻不懂得話中深意。
九十年代後期,家用電腦興起,他為我買了一臺電腦,說對學習有好處。而他自己也學會玩電腦遊戲“紅色警戒”,一手鍵盤,一手滑鼠,十分靈活。他會修理家電和維護電視設備,但已經跟不上時代,並不會修理電腦和軟體維護。五十歲的父親,和他們那代人一樣逐步被淘汰,調離了崗位。就這樣,慢慢過了幾年,六十歲的父親就退休了。
父親的人生就像天空劃過的拋物線。賦閑在家的他,組裝一個微型手搖發電機,逗鄰居家小孩玩。那時,智能手機興起。他已然沒有故障判別和修復能力。很多軟體不太會用。時常需要找我幫忙,我卻十分沒有耐心。
古稀的父親閒不住,在養護屋後坎上的枇杷樹時,不慎墜落五米多高的堡坎摔傷,身體多處骨折,頭部受到撞擊出血。鄰居發現後,叫來救護車把父親拉進了人民醫院。父親在重症監護室ICU裏,一直昏迷不醒。一個月之後,眼睛才微微睜開,三個月後方有些模糊意識……煎熬的好幾個月過去了,父親的病情漸漸得以好轉。但他的眼神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病榻上的他吃力地伸出左手,想要握我的手,就像想要抓住我蹣跚學步的時光。
經過一年多的治療,他的病情有所好轉,但他的眼神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偶爾也會露出無意識的笑容,似乎傳遞了他內心的力量與滿足。窗外河水靜靜流淌,父親也好像回到江邊的老家,回到了下鄉時的通江河。父親嘴角上揚時,又似乎回望著過去。
他艱難地伸出左手,想要握我的手,就像想要抓住我蹣跚學步的時光。他的手已那麼瘦弱,沒了任何力度。度過了死亡威脅的父親,偶爾也會露出無意識的笑容,似乎傳遞著他內心的力量與滿足。
這輩子過得平淡、普通,但又很堅定,一幀幀,一幕幕:童年的風箏飛揚在江邊上的鐵山坪,20歲那年隨著知識青年下鄉洪流,在那個叫做雲臺的地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兩年後,招工進了廠,參加到熱火朝天的三線建設中。青山廠,廠如其名,綠水青山,更因為偉大領袖教導,要咬定青山不放鬆。中年,普普通通的三口之家,廠子在汽車工業大潮下,軍轉民華麗轉身,發展不錯,孩子考上了理想大學……
當年那個22歲返城的小夥子,在他47歲的時候,在百貨商店買了口大瓷缸,送他19歲的兒子去飛行學院讀書。而今,他也成了個頭發花白的古稀老人,而他的兒子卻宛如28年前他的年歲。
時光機就這麼停駐在二十多年前,我邁出家門的那一刻。靜靜的河,淺淺的話,長長的路。河水晝夜不停息,多麼不可追。父母老了,我在努力彌補著空白的記憶。重疊的年歲,不同的記憶。
也許在我們眼裏,這一幕幕應該是這樣的:年幼時,父母遮風擋雨,扶苗剪葉。咿呀學語,笨拙的步伐,用單卡答錄機學拼音,笨鳥也飛了起來。他們攜我們走過小徑,扶助我們攀登山丘。時光機還記錄了我丟掉乳牙,是拋到房頂上的,小學數學和中學化學都拿到滿分。小城的人給我們工廠子弟取了個集體外號,叫青山水餃。沒有惡意的名字,但三線人的標籤早已烙印到了額頭。
如今,父親的雙手雖也不再像當年那樣厚實有力,但我依然記得那雙曾經給我帶來溫暖和力量的手——教會我的是做人的本分,傳承的是優良的家風。它們是我心中最珍貴的記憶,是我成長道路上最寶貴的財富。
- 記者:好報 編輯
- 更多生活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