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纱帐到收割机/赵秀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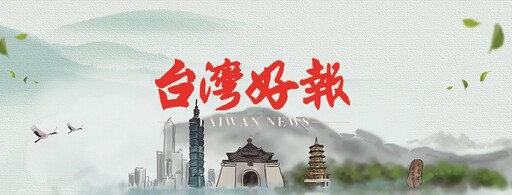
赵秀坡
和父亲通电话,得知老家近十亩玉米一天就收完了。父亲在电话那头感叹:“往年收玉米,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现在机器开进去,哗啦啦一阵响,玉米棒子就直接装车拉回来了,再也不用一穗一穗地掰了。”挂掉电话,那个金黄色的秋天又浮现在眼前。
那时的玉米地,真像一片无边的“林海”。一株株玉米如列队的士兵,挺拔整齐。硕大的玉米棒子半掩在或青绿或已枯黄的叶片间,宽阔颀长的叶子相互交织,连成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开收前,父亲总会用䦆头在玉米地中间砍出一条窄窄的通道,好让架子车能推进去。我们则“全副武装”——长袖衬衫、长裤、手工布鞋,父母还会用毛巾包住头,那模样,活像陕北的农民。
父亲给我们分了工,每人两垄,齐头并进。他话音刚落,我和哥哥便拎着化肥袋子钻进玉米林,立刻开始了比赛。伴随着清脆的“咔嚓”声,玉米棒子应声脱落,像一个个胖娃娃跳进袋子里。但总有那么几穗特别“倔强”,死死咬住秆子不肯下来,非得把整棵玉米杆拽弯了才勉强脱离。这时,父亲就会走过来示范:他左手稳稳托住玉米棒的根部,右手紧握棒身,顺势向下一拗——“啪”的一声,玉米棒便乖乖落入手心。他的动作干净利落,仿佛那不是劳动,而是一种手艺。
玉米地里密不透风,像个大蒸笼。不一会儿,汗水就浸透了衬衫,湿漉漉地贴在背上,又粘又痒。额上的汗珠滚进嘴角,咸涩难当。玉米叶子像无数把小锯子,在脸上划出细密的红痕,被汗水一浸,混着扬起的尘土,火辣辣地疼。可看着袋子渐渐被金黄的玉米填满,丰收的喜悦便压过了所有不适。我常常用袖子胡乱抹一把脸,又继续弯腰掰起来。
累了,就在地头歇口气。抱起白色塑料壶,“咕咚咕咚”灌几口凉白开,那滋味比任何饮料都解渴。我和哥哥会趁机在田边草丛里捉蟋蟀、逮蚂蚱。父亲则小心地剥开一穗特别饱满的玉米,细细数着上面珍珠般的籽粒,估算着今年的收成。从春播到秋收,他像照料孩子一样侍弄这些庄稼。哪棵苗弱了要追肥,哪片地旱了要浇水,他都记在心上。特别是暴雨过后,他总第一个冲进地里,一棵棵扶起倒伏的秧苗。“这块地不赖,亩产得上千斤!”数完玉米,父亲脸上绽开满足的笑容。
当架子车堆成一座小山,父亲便套上拉绳,弓着背在前头拉。我和哥哥在后面使劲推,车轮轧过土路,吱呀作响。一穗穗、一车车、一步步,我们把整个秋天搬回了家。接下来的日子,还要剥玉米、晒玉米、脱粒、磨面……母亲用新玉米面蒸的窝窝头,蘸着自家做的黄豆酱,那份质朴的香甜,至今仍是记忆中无可替代的美味。
如今,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取代了手工劳作的声响,半天工夫,十亩玉米地便一马平川。效率的提升毋庸置疑,只是那些浸透着汗水的苦乐时光,那些亲手触摸土地的温度,都随着滚滚黄尘飘远了。父亲偶尔还会说起从前,语气里既有对现代机械的赞叹,也藏着一丝对往昔岁月的怀念。那个需要全家出动、弯腰劳作十几天才能完成的秋收,终究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 記者:好報 編輯
- 更多生活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