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腦袋裡有實驗室的病毒,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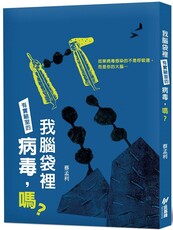

我腦袋裡有實驗室的病毒,嗎?
作者:蔡孟利 出版社:斑馬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7-20 00:00:00
<內容簡介>
基因工程發展至今,曾經在實驗室短暫出現過的奇形怪狀之病毒不知凡幾,沒有經過標準高溫高壓消毒程序而從排水管、從垃圾堆中流出的病毒又不知凡幾,誰又知道今日多少疾病是來自於這些不知凡幾的實驗室所廢棄或逃竄的病毒?如果,這些不知凡幾的病毒是有害的,但造成的不是立即知道要就醫的呼吸困難,而是,最難診斷出來的、介於明顯與不明顯之間的精神疾病呢?如果那樣的病毒默默地流行在每個人的腦子裡面,讓每個人默默地承受以為是自己人生的苦,這樣的瘟疫,又有誰能解?又有誰會想到要去解?
本書藉由一個實驗室的日常,呈現學術象牙塔內生活的枯燥與多變、固執與不羈、保守與熱情、念舊與創新等諸多衝突並存的特質,讓大眾得以一窺學術人的內心世界,以及這樣的內心世界所引領的研究對於這個世界所做出的,不知道是好是壞的貢獻。
★本書特色:
1. 如果病毒感染的不是呼吸道,而是你的大腦…
2. 人類苦難的降臨,可能只因為一個實驗室的認真或不認真
<作者簡介>
蔡孟利
台大動物學博士,現職為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教授,曾任《科學月刊》總編輯。是一個會做用在老鼠、蝦子、螃蟹身上的電極,也會寫小說和詩的中年人。
★內文試閱:
‧導讀
這是一本小說,純屬虛構的,但虛構的很真實,基本上可以算是一本實驗室的日常紀實。而如果讀者對於推理小說的定義沒那麼挑剔的話,本書也可以算是一本推理小說,或說是社會派的推理小說。當然,就如同我的前三本小說,其實我還是在寫愛情小說。
並不是我刻意讓這本小說呈現了如此多重的面貌,而是每個人在真實生活中本來就扮演了多樣化的角色,習慣每天換上一張張的面具面對一個個不同的人,在打躬作揖緊張忙碌不知所云的一天之後,忘了那一張才是真實的臉。即便在外人眼中像是活在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內的學術人,其實也是一樣的面具男女;所以只要幾近忠實的記錄這些人每天生活的點滴,日常就成了小說。
這本小說主角們的身份是科學家,忙的工作是科學研究,聽起來應該是很嚴謹又清高的一群。然而「學術研究」在今日已經是種規模龐大的產業,光是台灣的科技部在2020年補助基礎研究的專題計畫,總經費就超過一百億新台幣。而這個產業最主要的產品「學術論文」,近三十年來已經暴增到連專業研究人員都無法掌握的數量,甚至連挑選值得花時間閱讀的論文都成了研究的課題。
顯然,這個象牙塔的內部現在也擠滿了芸芸眾生,也因此,這個看似嚴謹又清高的行業,跟世俗中其它職場一樣,名利與情愛的煩惱也不會缺席。但又因為這個行業工作內容的特殊性與場域的封閉性,所以這些名利與情愛的煩惱常常也很象牙塔。像是實驗室中的宅男宅女大部分經歷的都是既不複雜也不太波折的愛情,可是當事人卻又很糾葛的深陷,就像本書中的男女主角們,第三者都不第三者了。
不過畢竟學術這一行的行規裡,發現與發明「新」的東西是主要的遊戲規則,可是「新」的產生,卻又來自於對「舊」的高度掌握;也因此,在學術這一行,枯燥與多變、固執與不羈、保守與熱情、念舊與創新這些看起來完全衝突的特質,卻是在這一行認真工作的人們每天不斷面對的衝突戲碼。在這本小說中,關於這部分的描寫,應該算是一部紀錄片那樣的寫實了。
小說裡引用了《金剛經》裡面的「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關於科學,希望讀者在看完本書後,也做如是觀。
‧推薦序
斜槓中年的奇妙冒險
我和蔡孟利學長認識,是在我碩士班一年級的時候。
那時我跨系考上電機所的醫學工程組,可以說是電機也不會,醫學也不會的新手。我找到了電機所和動物所(現在的生科所)的兩位老師聯合指導,但是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動物所。
指導教授嚴震東老師把我和蔡孟利學長編成了一組做同一個題目。如今思之,那應該是學長惡夢的開始吧。
學長是一個外粗內細的人,對於做研究很有自己的想法和堅持。我是一個生性比較閒散的人,一開始會覺得那麼認真要幹嘛。我過了好一陣子才逐漸體悟,這才是做研究的態度,因為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在和時間賽跑,實驗動物的成長不會等你,我們必須在最適當的時刻,取到最需要的數據。話雖如此,我還是常常粗心把實驗室辛苦養大的實驗大鼠弄死,讓學長只能苦笑著幫我善後。
相處久了,才知道學長的細膩,不只展現在動物實驗上。他有著溫柔而入世的文筆,說他是被生科耽誤的文學家也不為過。事隔多年,我再見到學長時,他果然已經成為出過好幾本書的暢銷作家,而他生物科技的本業也沒有荒廢。這樣的斜槓人生,看在與他近距離相處過的學弟我眼中,只能說非常適合他。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他曾為了正在撰寫的書中涉及法律的部分,特別來找我諮詢,我甚至還出了一份書面的法律意見書給他。對我來說,學長的嚴謹和堅持,在這件事情上表露無遺。我拜讀過學長之前的作品,我不敢保證每一個人都會喜歡他的書,但是我可以保證,他的每一字一句,都是經過這樣的態度雕琢出來的,在科普和故事性做到了最好的平衡。
說了一堆瑣事,也許還不足以對這本書的作者—蔡孟利學長做出最好的側寫,但是這的確是我以一個學弟的身分,對學長做出最真摯的觀察。欣見學長的新書又即將付梓,感謝學長給我這個在網路上專門博君一笑的律師這個機會留下隻字片語。期望以上文字足以代序,讓讀者更了解這本書的作者,作為踏入蔡式文學宇宙的第一步。
雷丘律師 斜槓律師的網路作家
‧摘文
第一章
最近,說不上是多久以來的最近,或許已經兩三個月了吧,常常在過了十字路口之後就停下來往回看,好確認一下是否有個剛剛路過的我倒在行人穿越道上,以確認此刻站在馬路這一端的我不是個遊魂,藉以告訴自己剛剛沒有闖紅燈也沒有發生任何交通事故而往生,在此刻的當下我的確是以一個「人」的身份於這裡顧盼。
不過通常這樣還是不足以對自己釋疑,在之後繼續往前走的幾百公尺內,我仍然需要不斷地頻頻回顧那個十字路口,掃描那個畫著白色線條的柏油路上到底有沒有任何事故發生的蛛絲馬跡,甚至掃描那些停等著紅燈轉綠的機車騎士們,看看他們的表情有沒有任何驚訝的樣子,好確保那個十字路口在我通過的時候沒有任何不幸發生,而我,與屬於我的那個肉體依舊是緊密結合。
這種奇怪的焦慮也不只是在十字路口才會出現,有時候在街上走著、在實驗室工作著,甚至在與學生講話的時候偶爾也會冒出來;沒來由的,忽然地就這樣質疑起自己,逼問自己目前所感受到的「我」究竟只是一團沒有實體的靈魂,或者,仍是一個有著完整肉身的「我」?而這樣的質疑不若剛走過行人穿越道的十字路口之情境,可以有個確認自己的肉體是否正橫躺在那個路口的現場;因為是那樣沒來由就想起來的質疑,以至於沒辦法隨時找到個可以檢核的目標。也因此這種質疑所帶來的焦慮就更加難以排除,得一直不斷逼自己回想之前的五分鐘、十分鐘、甚至是一個小時之前的所有細節,揣想是否有個被不經意忽略掉的閃失,導致「我」其實已經是個飄盪在人世間的遊魂而不自知。
我並不是沒有自覺到這可能是某種精神疾病的徵兆,諸如像是強迫症或是憂鬱症那類的。這些疾病我並不陌生,至少我讀過不下三百篇關於精神疾病的醫學文獻。倒不是因為我現在這個毛病,而是,讀那些文獻算是我工作的一部份,這個工作叫做「學術研究」。在學校給我的薪資通知單裡記載著我的薪水分成兩個項目,一個是「本俸」,另一個則是「學術研究」;因為「學術研究」的數額大於「本俸」,所以依薪資結構來說,「學術研究」算是大學老師的本務。而我這幾年關於「學術研究」的主要工作內容,就是在研究像是強迫症或是憂鬱症這類的精神疾病,到底是腦袋中神經細胞的哪些組成出了問題,只不過我的研究對象不是人,而是老鼠的腦細胞。
不是我多想知道老鼠的強迫症或憂鬱症是怎麼來的,而是,牠們的強迫症或憂鬱症是我造成的。我得想辦法讓老鼠發作些跟人的強迫症或憂鬱症很像的病徵,好對牠們的腦袋做功課,希望藉由了解牠們的發病機制來類推人類的強迫症或憂鬱症是怎麼發病的。
而我「學術研究」的主軸什麼時候從自主神經系統的調控轉變成為精神疾病的腦部病理,說起來也算是很意外的巧合,並不是經過什麼嚴謹的評估或是深思熟慮之後的結果。
基本上就只源於一次相親。那次的對象是一位臨床心理師,她雖然已經有了在醫院的正職工作,但同時也在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目前的研究主題是關於強迫症的研究,不過因為研究的對象是人,所以沒辦法把人的腦袋打開來做些實驗控制的操弄,因此也就沒辦法真正知道強迫症的腦袋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她說她一直在想是不是有可能拿老鼠來做動物實驗,這樣的話,就可以盡情地對腦袋進行各種手術與藥物的操作。
由於我通常會再約初次見面的相親對象二度吃個飯或是看看電影,一方面基於禮貌,另一方面也是給自己再次確認對方意願的機會。因此那天相完親之後,我找了些強迫症動物模式的文獻來看,也順便思考了幾個我自己實驗室的設備可以勝任的研究主題;想說,在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如果沒有其它適合的話題可以聊,就拿這些出來說說以避免冷場。
只是沒想到三天之後想要再邀約她,卻被她以工作太忙婉拒了。雖然理由說的是工作忙沒有空,不過依照我相親的經驗,那就是代表不需要再見了。不過也就這樣,意外地促使我打開那扇以前懶得去開的窗,發覺精神疾病的神經病理機制也是個可以試試的主題。所以在那年年底,我也就認真地寫了個老鼠強迫症的研究計畫,然後也通過了,有了一筆還不算少的經費,從此進入精神疾病的研究領域。
雖然說我覺得這種奇怪的焦慮應該算是一種精神病了,但為什麼會是現在才突然冒出來?回想起這幾個月的生活,我並沒有遇到什麼奇特際遇或壓力特別大的情境,甚至連個小感冒都沒有,生活一直處於算得上枯燥的規律,就只是出沒在教室、實驗室以及週邊那些跟日常食衣住行有關的商店而已,實在沒有任何夠份量的大事件會導致現在這樣疑神疑鬼的心理狀態。
會是遺傳的因素嗎?像原發性高血壓那樣,本來都好好的,也沒什麼身材走樣或是明顯的病痛,但是血壓就莫名其妙地在某一天忽然升高,然後接下來便是一輩子要吃降血壓的藥物。不過,如果是遺傳性疾病的話應該是有跡可循的,至少家族中的長輩或平輩應該會有苦於這類疾病的人,但是就我記憶所及,沒有印象在家族中有任何人有過精神方面的疾病。
當然也有可能的確是因為遺傳,只不過所有人的症狀都還在可以忍受的範圍之內,不需要求醫也不想跟旁人提起,所以別人也就無從得知。就像我現在這樣,雖然有些困擾,但還不至於到了干擾正常生活的地步,也因此除了在自已的腦海中轉轉之外,我不曾跟別人說過自己的感受。這是很有可能的,或許此刻我的親、堂、表兄弟姐妹們也有人跟我正承受著一樣的困擾,只是我們都隱藏得很好,也因此是不是遺傳疾病的突然發作,那就無從得知了。
如果真是這樣,有病,但是疾病的危害程度都在自我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那病或不病,其實也不是什麼需要太擔心的事情。不過我自己仔細回想這兩三個月以來的焦慮,程度上好像有越來越加重的趨勢。感覺上那種焦慮已經進展到不是眼見為憑就能釋懷,而是會進一步質疑正在重複著確認動作的自己是不是也已經死了?不斷地想著正在進行確認檢查動作的這個自己,會不會就像雙重夢境那樣,以為自己已經從一個驚險的夢境中醒來,後來卻發現那樣地醒來仍然只是一個更大夢境中的場景?
這樣子的演變,讓我對於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壓制這些念頭,好讓自己的外在舉止繼續正常到不至於讓別人察覺出異狀,我是越來越沒有把握了。
雖然有就醫的心理準備,不過如果真的需要就醫,我希望能夠至少撐到半年以後才去,畢竟接下來的這半年,會是我們這個研究能否成功的關鍵半年。我把升等的希望都押在這一系列的實驗上了,如果真能成功,不要說是升等,甚至拿個科技部的傑出獎都有可能。這個研究的進行是個難得的機會,我跟漢雄說,能不能離開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回到京城,就看這一搏了!到時候上了Nature,咱們兄弟倆一起開個記者會然後就跳槽,即便沒有T大,撈個Y大或C大,就算是Td大,也總比待在這個邊陲地帶好。
漢雄倒是每次都不置可否地回說:「看看吧,到時候再說。」
這的確是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六年前我初到這個學校面試的時候,一開始還把隔壁的國中當作是大學,因為論建築的大小跟氣派,那所明星國中比起隔壁這所剛從五專升格的大學還像大學。而被錄取之後的第一天,系主任帶我到一間三坪大的房間,裡面除了一張桌子、一張椅子還有一台擺在桌上的電腦之外,其它的,就只有家徒四壁可以形容了。然後,沒什麼用來草創實驗室的開辦費用,主任說一切自己想辦法,系上能給的,大概就每年例行均分的設備費四萬元而已。然後他拍拍我的肩,說了句:「年輕人,加油,本系就靠你了。」
漢雄晚我半年進來,雖然他錄取的是另外一個系,不過狀況也沒有好我到哪裡去,就只是他分到的空間有四坪,比我的三坪多了兩塊榻榻米大的地板。
由於我們算同梯進來這個學校,基本上比較容易聊得上話。加上我們的研究領域都是跟神經科學有關,主要差別只在於我的工具是分子生物學方面的,漢雄則是對整隻老鼠插電線的電生理。也因此一開始兩個人在研究上的互動與討論就比較密切,一直想著有什麼題目可以共同合作。畢竟初來乍到這樣一個毫無資源的地方,面對那些一副就準備把你當助理使喚的地頭蛇大老,兩個菜鳥自然需要團結些。
只不過,兩個都沒有糧草的菜鳥,除了抱怨的時候有能力團結以外,談合作,空對空,有什麼好合作的呢?
所以在開始的前兩年,我和漢雄除了週間有一個整天沒課的日子之外,加上週六、日兩個假日,每週有三天得長途驅車到京城去依親做實驗;漢雄回他博士班的老闆那邊借用,我則是到我博士後的老闆家掛單。每週有大把時間花在各式縣道、省道與國道上的風塵僕僕,每半年汽車增加的里程數都在一萬公里以上,開車開到連公路上每根測速照相機與每個紅綠燈所在路段的里程標示都記得清清楚楚。
而「合作」,在當時是遙遠不可及的未來,每次聊起來,都是灰姑娘在晚上十二點以後的心情。
由於都是寄人籬下,基本上自主性不高,雖然老闆寬宏大量讓出通訊作者的位置讓我可以實質累積發表的數量,不過研究的內容還是得謹守老闆的需求,畢竟花用的錢財和差使的人力都是老闆所供應的。不過也算歲月靜好,雖然有著奔波的辛勞與那麼點無法作主的不自由,撐了四年,我跟漢雄還是都站上了副教授的位置,擺脫了尷尬的「助理」二字加在「教授」前面。
當然這中間免不了有些閒言閒語不時地飄過來,譏諷著我們都不想在這個學校落地生根好好經營在地的實驗室,批評我們滿腦袋就只想著跑去京城打關係鋪跳槽的路,根本無心留在這裡工作、教育這裡的學生。我能說什麼呢?學校的補助費都被這些講風涼話的地頭蛇大老們劫走,每次能分到個三、四萬的零頭已經是他們對我莫大的施捨了;而國科會給的計畫經費了不起百萬出頭,扣掉給學生的工讀費,連台像樣的光學顯微鏡都買不起。現實就是這樣,不出門找外援,難道要在這裡等著被人家用六年條款宰割。
每次被這些閒話搞得火大時,漢雄都是都一笑置之地回我說:「管他們去死。」
「但他們就是想我們在這裡悶死。」
「實力原則。當你的實力夠強大時,他們頂多叫叫,不敢咬你。」漢雄輕蔑地對空笑了笑,又補了一句:「我學長講的。」
現實的確是這樣。只是我漸漸知道「實力」的定義不單單只是學術研究的產出,也不單單只是受學生歡迎的程度,還得包括拉幫結派的廣度、揣測上級心意的準確度,更重要的,還有在五斗米之前折得下腰的角度。
論文在這個學校是弱勢貨幣,只靠這個,我跟漢雄在這個學校仍然買不到該有的權益與公平的對待。日子在這種沉悶的懷才不遇中過起來,就好像每天都測準了股市起落而存款卻買不起一張台積電。也因為如此,「相親」這件事情在這種枯燥無奈的生活中,就變成了少數可以轉換心情的喘息時刻,彌補了我因為不想有師生戀、也不想吃了窩邊草而影響在掛單處的人和,所造成無法與異性進一步交往的缺憾。
說到這點,漢雄就比我悲情多了,他來這個學校任職的第一年本來要結婚了,未婚妻卻在婚禮前的三個月出家去了,從此,他也成了一位老僧。
但這位老僧的入定在我看起來並不是真的老僧式入定,而是,因重大創傷而導致的極度自我防衛,關閉了對大部分世事感知的興趣,以避免傷重的心神又不斷地被各種有所謂與無所謂的俗務拉扯而無法復原。也因此,當他說「管他們去死」的時候,我猜他的意思其實是「我已經死了,無所謂」。
有別於我是真的憤世嫉俗地看不起他們而管他們去死,因而容易被那些我不想管他們去死的他們心生仇怨,以至於他們會用更進一步的挑釁態度來測試我的能耐。而漢雄那種「我已經死了,無所謂」的管他們去死,反而讓那些他們心生畏懼,覺得這個年輕人是不是有什麼硬挺高聳的靠山撐著,才能夠這麼毫不在意地不搭理世事的傲嬌視人。
但是儘管我多了相親這個管道,一直到了快四十有二的今天,我的感情也沒有比漢雄這位老僧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窩在這麼一個鳥不生蛋的小地方,自然地就阻絕了這個地方以外的女生想要繼續交往的意願;演化論講地理隔絕不是沒有道理的,不要說高山與海峽那種天然障壁,光是約會之前要趕的路程超過六十公里,就足以形成約會時間難以契合的自然隔絕。
畢竟,不是學生時代的聯誼,而是已經有著忙碌工作的職場男女交往,而且是在適婚年齡的時間壓力下有目的之交往。因此那六十公里,意謂的不僅是約會時間契合上的困難,也意味著將來若是在一起了,一定有一方原有的生活會被這六十公里嚴重破壞,不管是我遷就她或是她遷就我,都會打亂一個家庭本來應該有的生活秩序。
我在多次相親之後終於認清了這個現實,亦即,若想成功,得在這個小地方找。但是這樣不僅大幅限縮了可以相親的人選,而且,即便已經在這裡待了六年,我還是不放棄任何可以班師回朝的機會,若是一但找了這裡的人成了家,那麼就得放棄回京任教的可能;也因為多了這層考慮,漸漸地「相親」就變成是純粹為了相親而相親,不僅自己懶了,連帶地幾位熱衷介紹的長輩與朋友也覺得累了。
「相親」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條件卻極其嚴苛的考驗。或許就跟荷爾蒙與受體相遇一樣吧,一開始環境的條件得要適合,就像人類的體溫要維持在攝氏37度上下,讓荷爾蒙與受體這兩種分子的結構穩定,也剛好供應足夠的能量,讓荷爾蒙的運動速度快到足以維持與受體的高碰撞機率。而且相逢需要緣份,因為相對於它們所存在的空間來說,荷爾蒙很少,少到像在底面積是七個足球場、高度是101大樓那樣的廣闊空間裡,一個人隨機地來回穿梭,看看會不會剛好就撞到站在地面上那個以受體為名的人。也因為是這樣地渺渺茫茫,所以真的要相遇,除了靠環境條件許可下的隨機運氣之外,還得要有一些冥冥之中互相吸引的緣份—就像是各自帶有正、負電的先天印記,讓彼此於茫茫的分子海中,感覺得到對方的牽引。
這其實是漢雄的思考風格,寓生活以生物學,有時候我也會不自覺地受他影響而以這樣的邏輯思考。
「細胞內任兩個分子的碰撞,都可以算是隨機般的偶然緣份,但是在細胞那個有限體積的空間內,這些隨機般的偶遇,又會累積成命中注定般的必然。所以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跟那些酶、幫浦、轉運蛋白、離子通道什麼的沒兩樣,都只是在大環境中不知不覺地照著被命定的方向隨機飄蕩而已;看起來有跡可循,但是骨子裡又是那麼地隨機;說是隨機,卻又擺明了像是照著劇本走。」這是昨天漢雄說的。
這兩年升上了副教授,或許壓力小了點,他也開始恢復點「人性」,好像比較能夠放下他未婚妻出家的陰霾,偶爾聊聊他對感情的體悟。
「生物學大概會用『演化』來理解這種看似刻意的隨機過程;人生呢,也許就用『因果輪迴』吧。」漢雄接過服務生遞來的飯後咖啡,邊把杯子放下邊說。
「那你真的相信『因果輪迴』嗎?像現在,我們坐在這邊談的這些話,也是輪迴的因果造成的嗎?我是說,一個小時之前,我和你兩個人都在各自的教室上課,沒有事先約,結果現在我們居然就坐在這裡聊了快一個小時,這是現在這輩子隨機般的偶然事件呢,還是跟上輩子或是上上輩子有關的因果輪迴?有沒有可能我們今天的見面真的只是在這輩子的這段時間內,很單純的獨立事件,完全跟上輩子或是上上輩子都沒有關係呢?」昨天中午上完課外出覓食的時候,碰巧在校門口看到漢雄也在覓食中,剛好兩個人下午都沒課,所以就一起到附近的西餐廳吃個飯;聊到了我最近一次的相親,結果東拉西扯的,就扯到了因果輪迴。
「應該沒有這輩子忽然才出現的事情。」漢雄拿著湯匙攪拌著剛送上來的卡布奇諾,以他慣有凝視虛空的渺茫神情說:「如果我們把萬物,包括人,都拆解到最基本的組成元件來看,就是那張元素週期表內幾種原子的集合罷了。以前國中就學過物質不滅定律吧,就那樣,地球上這些原子基本上只是在各種不同型態的結構中流轉來流轉去,就像是,我們身上的那些碳原子,其實很難搞清楚哪幾顆在昨天還只是存在於路邊一隻狗掉下來的皮屑、而哪幾顆又是來自於一百年前這裡的一根草的細胞壁。就這樣,我們今天這個形體所用的材料,都是在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甚至更久更久之前就存在於某個東西內,而且其中也一定有一些是用在很久很久之前的某個人身上。」
「所以你是說,碳原子也會帶著記憶囉?關於它曾經在誰身上待過的那些事情。」
「其實,『記憶』這個詞很特別,我們都是幹這行的,應該很清楚這個詞根本說不清楚。對於一件我們怎麼想都再也想不起來的事情,比如說,如果我問你,在十年前的今天下午一點你說過了哪些話?一定不會記得,是吧;那,這樣子,我們對於十年前的今天下午一點所說過的話到底還有沒有記憶呢?」漢雄停止了攪拌的動作,緩緩地呼出了一口氣,直直注視著杯內的卡布奇諾泡沫說:「所以,到底什麼叫做『記憶』呢?」
沒等我回話,漢雄忽然從口袋中掏出掛著一串鑰匙的鑰匙圈,摸了摸掛在上頭一顆汽車形狀的隨身碟,繼續看著卡布奇諾的泡沫說:「我身上帶著的這顆隨身碟,裡面少說也存了上百個檔案,那我能說,因為這顆隨身碟記得了上百件事情,所以隨身碟有記憶,嗎?」
「實際上來說,應該算有。」
「但是,如果沒有找到一台電腦,我們就不會知道這顆隨身碟裡面到底記憶了什麼,是吧?當然啦,現在電腦沒那麼難找,好,我弄來一台了,問題是,灌的軟體版本不對,結果一開檔案,哇卡,都是亂碼,開出一堆奇怪的符號和看不懂的字。那,它還是當初我存入隨身碟裡面的那個『記憶』嗎?在那個當下,我的隨身碟,它真的記憶了我認為它該記憶的東西嗎?」
「那就找一個能夠正確開出它的版本啊!」
「如果都找不到呢?」
「那就沒辦法了。」
「如果沒辦法的話,那這樣,這個隨身碟到底還有沒有記憶呢?」
沒等我回話,一問完,漢雄立即接續著說:「如果,我把這個殼撬開,露出裡面的電路結構,然後把它們放到各種很厲害的顯微鏡底下,仔細地檢查那些電路結構,甚至用電極檢查每一條線路的導電狀況,那這樣,我既看得到隨身碟內的所有零件組成,也能描述它們運作時的電流迴路,那這樣我是否能夠說,經由這些分析,我就可以知道存在這個隨身碟裡面的記憶是什麼?」
「聽你這樣說,倒像是《金剛經》裡面說的『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
「對,就是這樣的感覺沒錯,你引用得真好!」漢雄眼睛離開卡布奇諾泡沫,抬起頭瞟了我一眼,笑了一下,但隨即又將笑意收起來,繼續低下頭去盯著那坨泡沫,說:「不過還有個更棘手的問題,就是,如果哪天這根隨身碟掉到地上,結果啪的一聲解體了,裡面儲存檔案的晶片掉了出來,雖然晶片沒摔壞,但是隨身碟其他部分都散了,晶片再也裝不回去。那,這樣就算找了電腦過來也沒用,這塊晶片是絕對沒辦法塞到電腦的任何一個插槽內讀出檔案。那麼,一塊讀不出來的晶片,它還能算存有記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