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達土地問題卡關 該檢討什麼?──市場機制和公平鑑價難以解決
輝達(NVIDIA)想在台灣設立海外總部,幾個地方都想爭取,半年前台北市政府用已租給新光人壽的北士科T17及T18土地,爭取到輝達同意在台北設立總部。但隨後這項方案出現了甚大的困難,連經濟部都必須出馬設法找出其他可能的用地以把輝達留在台灣。這事件再一次顯示土地問題對台灣經濟的干擾,相關政策的不公平性,以及相關部門政策草率可能造成的傷害。
輝達案該檢討的三種做法
本文不是要追究任何人員或機關的責任,而是要藉此說明輝達案中三種該檢討的做法:政府把土地租或賣給企業時,可能價格偏低而使購買者得到不當利益;政府把投資案鎖定在特定土地,而使地主用獨占力謀求不合理利益;政府不釐清問題根源,而用威權脅迫的態度取代民主法治來重新分配不當利益。輝達即使能很快順利投資,這三種做法仍應繼續檢討改善。
土地是特殊的生產要素,土地的價值很大一部分決定於它的位置,而位置是沒辦法改變的,再加上整個社會具備類似條件的土地供給量有限,且可能被少數人掌握,因此土地問題常包含很多獨占及不公平競爭的問題,不像其他資源或產品可以利用市場自由競爭的機制,來公平解決該由誰運用及誰該得到多少報酬的問題。長期以來各國政府都知道要由政府適度介入土地問題,但介入不當時也常會造成其他不公平和低效率的問題。輝達投資案就是個例子。
一、是否使購買者不當得利
先來看一個朋友在某國投資的故事,因為它可以很簡單顯示土地利益的問題。該國本來幾乎由政府控制所有土地,而在尋求經濟發展之後,就由政府把一些土地低價批給要投資設廠的人運用。這位朋友有一天接到當地有良好關係的縣長電話,說要把某塊土地批給他,他說目前他並不需要這塊土地,縣長說沒關係,你先批下來,會有人高價找你買。至於這位朋友最後有沒有買及需不需要分多少利益給縣長,朋友沒告訴我。政府低價批土地給投資者本來是要鼓勵投資,但土地可以轉讓時,批到土地的人就可以用更高價轉給真正需要的別人而獲取暴利,甚至阻礙了正常可有的投資。T17和T18當年若未租給別人,輝達總部現在可能已規劃完成而將可動工。
從這個角度看,由政府保有土地,而在適當的時候依公正價格賣給真正要做投資的人,有可能是較合理的政策。但現實上適當的時機以及公正的價格卻不易掌握,因此由政府直接出售土地給投資者也常會有爭議。官員為了降低自己的責任或圖利的嫌疑,可能選擇先把土地以標售或其他有市場機制的方式把土地賣給民間業者,再由業者去把土地轉賣或轉租給真正需要土地的人。但經這樣一手並不見得能使分配更為公正合理,因為政府賣出的價格及業者再轉售的價格,都不是在真正自由公平競爭下進行,其間常會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
二、是否使大財團或地主不當得利
政府賣出時就算採公開標售,通常也會附一些條件而可能形成綁標,並由特定人低價得標。而土地面積及價值甚大時,通常也只有大財團買得起,因此大財團也常可用較低價取得。而除非市場上有甚多類似的土地相互競爭,否則取得土地的人也會取得一點獨占力量,而可以向真正要在這土地上投資的人索取更高的價格。如果政府忽視這獨占力,很自信或草率地把某個投資者媒介和限制在某塊特定土地,卻未能先講好價格,則投資者就可能被擁有土地的人完全壟斷,而需付出更高的價格。這就會造成不公平,投資者不願當寃大頭時也會使交易談判的時間拉長而延誤投資。台北市政府當時沒講好價格和相關條件,就決定輝達要在T17與T18建總部,可能就是不懂或忽視這種不公平競爭或獨占力量的問題。
有人認為可由公正機構來決定公正合理的價格。但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引進公正的仲裁或鑑價機制也難解決。其主要原因是有一部分條件或價格已先決定,以致這土地公正合理的價格和地主公正合理的報酬率,這兩個公正合理,很可能難以同時符合即定的條件。
用一個虛擬的數字例來說明。假設A市政府把一塊土地用30億元租給B公司50年,而現在B公司要以130億元轉租給C公司50年,B公司不必做什麼事就賺進100億元,必使人民覺得不公平。而若一個有能力且公正的機構算出公正合理的報酬率應為50%,則B公司可用原來成本加50%即45億元的價格將土地轉租給C公司,而在表面上好像公正合理。但事實卻不一定。因為這塊土地依現在市場推估的合理租金並不一定恰好也是45億。若公正合理的租金較高,45億的租金即可能是圖利C公司。若公正合理的租金較低,則C公司即被敲詐或不願意承租。
這種兩個公正合理條件很可能互相矛盾的情況,只要把兩種合理價格間的差距交給市政府,或由市政府補貼,似可以解決。例如前例中公正的市價若為80億,則C公司出80億來租,市政府收取35億,而B公司收到符合公正報酬率的45億,則兩項公正合理條件可同時滿足。所以A市府也許會想改變或廢除原來對B公司的租約,以上述分配來同時達成這例子中的雙重公正合理條件。
但B公司因為有契約和法律保障而很可能不答應。B公司若在30億之外還曾付出了一些不能公開的成本,它更不可能答應而在實質上受損。A市府若用各種政治或威脅手段要B公司改約或廢約,則像是威權統治而不符合民主法治的規範。而這種做法也可能變相證實原先A市府只用30億把這土地租給B公司的決策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因此可能引起其他政治爭議。
如果只算公正的租金而不去管B該得的合理報酬率,也就是在上例中強迫B公司以80億賣給C公司,B公司表面上委曲,實質上仍多得了35億的不公平利益,人民也很可能不願接受這種不當利益的存在。
三、是否造成重新分配的不當得利
上述分析和簡化的例子和輝達案顯示,政府把土地租或賣給民間,再由民間轉租轉賣的做法,很可能會出現不公正不合理甚至舞弊的現象,所以未來政府應該儘量避免。政府把投資者和地主配對,再由它們自行協商價格的做法,也可能創造地主更大的獨占力量。
所以政府在土地配置問題上不該隨便把責任推給市場,或要相關企業自行與地主協商。特別是為因應重大投資所需的大面積土地,政府最好能持有較多存量,並研擬較公正合理的評價機制,再儘量以合理的價格賣給真正需用土地的投資者,不要再把責任推給不可靠的市場機制。如果投資案對國家社會具有較大的外部利益,即使評價無法很精準而讓投資者得到一點額外利益,人民應該也比利益被中間地主拿走的情況容易接受。
台灣以前也用政府開發產業園區或出售台糖及其他公有土地的方式,來支援產業投資,並有不少成功,但其中當然也有不少政商勾結圖利的情況。不過設計更好的監督及評價制度以降低這類圖利問題,以及檢討追究以前圖利的案例,可能仍比藉口市場機制而把政府土地隨便賣出,或隨便把投資者和地主送做堆而讓他們相互爭執,更可能接近公平合理。
土地這種容易藉不公平競爭而獲利,特別是讓財團獲利的情況,在不少土地政策上都可能出現。例如容積率的移轉,都市計畫和容積率的變更,以及都市更新的獎勵等等,都常要大規模的財團才較能運用而獲利。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盤點一下過去的案例,看看各種政策獎勵有多少比例是被有辦法的人或財團拿走。在台灣地價問題已經被認為造成社會重大不公平的情況下,各項可能對財團較有不合理利益的土地相關政策,都應該仔細檢討改善,不要以自由市場之名,而造成較有錢的人和財團可獲得更多不公平之利益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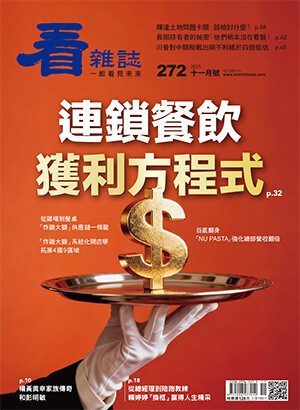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272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看》雜誌 第272期)謝謝!
輝達案該檢討的三種做法
本文不是要追究任何人員或機關的責任,而是要藉此說明輝達案中三種該檢討的做法:政府把土地租或賣給企業時,可能價格偏低而使購買者得到不當利益;政府把投資案鎖定在特定土地,而使地主用獨占力謀求不合理利益;政府不釐清問題根源,而用威權脅迫的態度取代民主法治來重新分配不當利益。輝達即使能很快順利投資,這三種做法仍應繼續檢討改善。
土地是特殊的生產要素,土地的價值很大一部分決定於它的位置,而位置是沒辦法改變的,再加上整個社會具備類似條件的土地供給量有限,且可能被少數人掌握,因此土地問題常包含很多獨占及不公平競爭的問題,不像其他資源或產品可以利用市場自由競爭的機制,來公平解決該由誰運用及誰該得到多少報酬的問題。長期以來各國政府都知道要由政府適度介入土地問題,但介入不當時也常會造成其他不公平和低效率的問題。輝達投資案就是個例子。
一、是否使購買者不當得利
先來看一個朋友在某國投資的故事,因為它可以很簡單顯示土地利益的問題。該國本來幾乎由政府控制所有土地,而在尋求經濟發展之後,就由政府把一些土地低價批給要投資設廠的人運用。這位朋友有一天接到當地有良好關係的縣長電話,說要把某塊土地批給他,他說目前他並不需要這塊土地,縣長說沒關係,你先批下來,會有人高價找你買。至於這位朋友最後有沒有買及需不需要分多少利益給縣長,朋友沒告訴我。政府低價批土地給投資者本來是要鼓勵投資,但土地可以轉讓時,批到土地的人就可以用更高價轉給真正需要的別人而獲取暴利,甚至阻礙了正常可有的投資。T17和T18當年若未租給別人,輝達總部現在可能已規劃完成而將可動工。
從這個角度看,由政府保有土地,而在適當的時候依公正價格賣給真正要做投資的人,有可能是較合理的政策。但現實上適當的時機以及公正的價格卻不易掌握,因此由政府直接出售土地給投資者也常會有爭議。官員為了降低自己的責任或圖利的嫌疑,可能選擇先把土地以標售或其他有市場機制的方式把土地賣給民間業者,再由業者去把土地轉賣或轉租給真正需要土地的人。但經這樣一手並不見得能使分配更為公正合理,因為政府賣出的價格及業者再轉售的價格,都不是在真正自由公平競爭下進行,其間常會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
二、是否使大財團或地主不當得利
政府賣出時就算採公開標售,通常也會附一些條件而可能形成綁標,並由特定人低價得標。而土地面積及價值甚大時,通常也只有大財團買得起,因此大財團也常可用較低價取得。而除非市場上有甚多類似的土地相互競爭,否則取得土地的人也會取得一點獨占力量,而可以向真正要在這土地上投資的人索取更高的價格。如果政府忽視這獨占力,很自信或草率地把某個投資者媒介和限制在某塊特定土地,卻未能先講好價格,則投資者就可能被擁有土地的人完全壟斷,而需付出更高的價格。這就會造成不公平,投資者不願當寃大頭時也會使交易談判的時間拉長而延誤投資。台北市政府當時沒講好價格和相關條件,就決定輝達要在T17與T18建總部,可能就是不懂或忽視這種不公平競爭或獨占力量的問題。
有人認為可由公正機構來決定公正合理的價格。但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引進公正的仲裁或鑑價機制也難解決。其主要原因是有一部分條件或價格已先決定,以致這土地公正合理的價格和地主公正合理的報酬率,這兩個公正合理,很可能難以同時符合即定的條件。
用一個虛擬的數字例來說明。假設A市政府把一塊土地用30億元租給B公司50年,而現在B公司要以130億元轉租給C公司50年,B公司不必做什麼事就賺進100億元,必使人民覺得不公平。而若一個有能力且公正的機構算出公正合理的報酬率應為50%,則B公司可用原來成本加50%即45億元的價格將土地轉租給C公司,而在表面上好像公正合理。但事實卻不一定。因為這塊土地依現在市場推估的合理租金並不一定恰好也是45億。若公正合理的租金較高,45億的租金即可能是圖利C公司。若公正合理的租金較低,則C公司即被敲詐或不願意承租。
這種兩個公正合理條件很可能互相矛盾的情況,只要把兩種合理價格間的差距交給市政府,或由市政府補貼,似可以解決。例如前例中公正的市價若為80億,則C公司出80億來租,市政府收取35億,而B公司收到符合公正報酬率的45億,則兩項公正合理條件可同時滿足。所以A市府也許會想改變或廢除原來對B公司的租約,以上述分配來同時達成這例子中的雙重公正合理條件。
但B公司因為有契約和法律保障而很可能不答應。B公司若在30億之外還曾付出了一些不能公開的成本,它更不可能答應而在實質上受損。A市府若用各種政治或威脅手段要B公司改約或廢約,則像是威權統治而不符合民主法治的規範。而這種做法也可能變相證實原先A市府只用30億把這土地租給B公司的決策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因此可能引起其他政治爭議。
如果只算公正的租金而不去管B該得的合理報酬率,也就是在上例中強迫B公司以80億賣給C公司,B公司表面上委曲,實質上仍多得了35億的不公平利益,人民也很可能不願接受這種不當利益的存在。
三、是否造成重新分配的不當得利
上述分析和簡化的例子和輝達案顯示,政府把土地租或賣給民間,再由民間轉租轉賣的做法,很可能會出現不公正不合理甚至舞弊的現象,所以未來政府應該儘量避免。政府把投資者和地主配對,再由它們自行協商價格的做法,也可能創造地主更大的獨占力量。
所以政府在土地配置問題上不該隨便把責任推給市場,或要相關企業自行與地主協商。特別是為因應重大投資所需的大面積土地,政府最好能持有較多存量,並研擬較公正合理的評價機制,再儘量以合理的價格賣給真正需用土地的投資者,不要再把責任推給不可靠的市場機制。如果投資案對國家社會具有較大的外部利益,即使評價無法很精準而讓投資者得到一點額外利益,人民應該也比利益被中間地主拿走的情況容易接受。
台灣以前也用政府開發產業園區或出售台糖及其他公有土地的方式,來支援產業投資,並有不少成功,但其中當然也有不少政商勾結圖利的情況。不過設計更好的監督及評價制度以降低這類圖利問題,以及檢討追究以前圖利的案例,可能仍比藉口市場機制而把政府土地隨便賣出,或隨便把投資者和地主送做堆而讓他們相互爭執,更可能接近公平合理。
土地這種容易藉不公平競爭而獲利,特別是讓財團獲利的情況,在不少土地政策上都可能出現。例如容積率的移轉,都市計畫和容積率的變更,以及都市更新的獎勵等等,都常要大規模的財團才較能運用而獲利。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盤點一下過去的案例,看看各種政策獎勵有多少比例是被有辦法的人或財團拿走。在台灣地價問題已經被認為造成社會重大不公平的情況下,各項可能對財團較有不合理利益的土地相關政策,都應該仔細檢討改善,不要以自由市場之名,而造成較有錢的人和財團可獲得更多不公平之利益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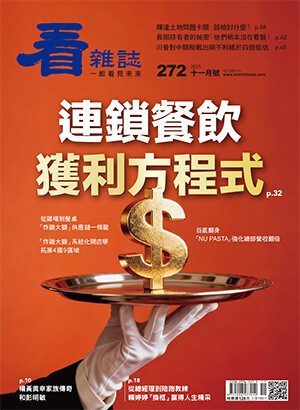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272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看》雜誌 第272期)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