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蒙山下箜飯情/付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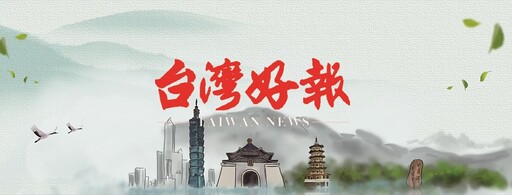
付令
落日餘暉裏,炊煙漂浮在烏蒙山的村寨。一縷縷青煙扭著細腰鑽進雲層時,鐵鍋裏的故事便開始了。老人們說,百年前大旱,名叫阿箜的姑娘將寨裏最後的半袋米倒進鐵鍋,又添了後山的蕨菜、崖縫裏的蘑菇、溪邊的水芹菜。當鍋底結出第一塊金黃鍋巴時,人們枯瘦的臉龐突然被香氣照亮——米粒吸飽了山野的精華,焦脆的鍋巴在齒間迸出五穀的甜,這道救命的飯食從此被稱作“箜飯”。
而今,我真的站在了老灶台前,看楊阿婆枯枝般的手指在鐵鍋上方翻飛。臘肉片在熱油裏捲曲成月牙,土豆塊漸漸染上夕陽的暖黃,青豆入鍋時迸裂的脆響,似乎能聽見當年阿箜數米粒時的聲聲歎息。山泉水漫過米堆的刹那,整口鍋忽然變成微縮的烏蒙山:紅辣椒是裸露的丹霞,紫茄丁是暮色中的野莓,而那層慢慢凝結的鍋巴,分明是梯田在晨光裏泛起的漣漪。阿婆總要等灶膛裏的柴火轉為文火,才撒下最後一把野香蔥,青翠的碎末在蒸汽中起舞,宛如山風掠過竹林時抖落的綠影。
最難忘是兒時某個星期天,同學阿強的父親帶著滿身煤灰推開家門,黢黑的掌心裏卻托著塊完整的鍋巴。那些嵌進焦殼的指紋溝壑裏,蓄著井下八百米的潮寒與灶台邊的暖意。我們像啃月餅似的慢慢啃食那片金黃,煤渣的粗糲混著米香的甜。每當鍋鏟刮擦鍋底的聲響傳來,我總會下意識回頭,仿佛那個渾身煤灰的漢子還會笑著從口袋裏摸出油紙包。
去年老同學阿強寄來真空包裝的箜飯包,電磁爐上的玻璃鍋卻煮不出記憶中的味道。那些規整的米粒拒絕吸收湯汁的滋味,臘肉片保持著工業切割的冷漠,甚至連鍋巴都結得心不在焉。原來,真正的箜飯需要吊腳樓漏進的穿堂風調味,需要柴火在鐵鍋底繪出的火焰圖騰,更需要簷角那只總來偷看的喜鵲作見證。就像寨子裏人們說的:“箜飯是聽得懂山歌的,電磁爐那玩意兒,哼不出我們烏蒙的調調。”
楊阿婆說要教我們做“真正的箜飯”。她顫巍巍從梁上取下熏了三年的老臘肉,又讓我們去溪邊採摘折耳根。“你看這鍋,”她蒼老的手指撫過鐵鍋凸起的補丁,“好幾十年了。”當混合著豬油、山泉和歲月包漿的蒸汽升騰而起時,老人突然哼起一支我聽不懂的歌謠,沙啞的嗓音裏晃動著明滅的火光。後來才知道,那是村寨裏人人會唱的歌謠,講的是阿箜姑娘讓米粒變甜的傳奇。
烏蒙山區的傍晚,鐵鍋在灶上咕嘟咕嘟地冒著氣泡。米粒吸飽湯汁的沙沙聲,像極了山神在翻閱泛黃的史志。鍋巴撬起的脆響驚亮了路燈,整個村寨便浸在琥珀色的光暈裏——阿箜姑娘的機智,楊阿婆的堅守,阿強父親掌心的溫度,都在這口鐵鍋裏完成了輪回。
- 記者:好報 編輯
- 更多生活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