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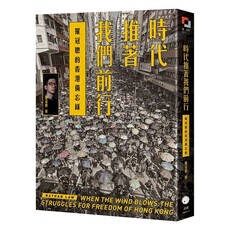

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
作者:羅冠聰 出版社:黑體 出版日期:2024-08-07 00:00:00
<內容簡介>
時代將他推上浪頭,他也引領著時代前進。
年僅31歲的他,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縮影。
從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到流亡海外的香港抗爭要角,
在港府的追捕之下,他如何持續奮戰?
身在異鄉,他是否也懷念香港的美好事物?
羅冠聰最真誠的自畫像,描繪成長過程和流亡的經歷。
「我想擺脫『流亡』附帶著的那種無力、滄桑、被動的標記──
我的選擇,是一種戰鬥。」──羅冠聰
羅冠聰是當今最為人知的香港民主運動人士之一。他曾是雨傘運動中的學生領袖,也曾創立政黨「香港眾志」,並當選為立法會最年輕的議員。
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來,羅冠聰就不曾缺席香港民主運動的征途。但面對《港區國安法》的步步進逼,他選擇離開深愛的香港、流亡英國,並持續在國際上為香港議題發聲奔走。
本書是羅冠聰首部結合回憶錄、流亡筆記和政治評論的著作,他不僅回顧自己的童年和家庭生活,也敘述遠赴美國求學,乃至於決定離港流亡背後的心路歷程。面對中共和港府的打壓、外界的質疑和攻擊,羅冠聰也寫下自己的內心感受和所思所想。
這是羅冠聰寫給這個時代的香港備忘錄,提醒著世界,牆外仍有人在點燈前行,照亮香港的黑暗。
★本書特色:
☆ 羅冠聰最真誠且深入的自我剖白,全球獨家出版。
☆ 收錄數十張珍貴照片,帶你看見最真實的羅冠聰。
☆ 結合個人回憶錄、流亡筆記和政治評論,豐富你對香港抗爭的視野。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桑 普︱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
各界推薦
矢板明夫︱日本資深媒體人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
汪 浩︱國際政經專家
林昶佐︱前立法委員、閃靈樂團主唱
苗博雅︱台北市議員
曹興誠︱著名企業家、聯華電子創辦人
羅永生︱香港文化研究學者
(依姓氏筆畫排列)
★目錄:
推薦序 時代推著他前行,他亦推著時代前行/桑普
自序 時代就這樣倒退著
第一部 時代之間
時代就這樣推著我們前行
一、 迷霧一年
二、二○一九
三、無盡抹黑
四、遠方求學
五、寒冬將至
第二部 流亡
一、 兩道閘門
二、肝膽崑崙
三、光輝歲月
【插曲】足球故事
四、歷史會面
五、面對焦慮
六、煙火綻放
七、尋求庇護
【投書】我離開香港,是為了告訴英國關於中國的真相
八、倡議之外
九、踏上征途
十、身分認同
【講稿】我們的前路,由我們決定
十一、無愧於心
第三部 異鄉
一人之境
真誠才是最大本領
一籠燒賣
牌愈爛,就要愈比心機打!
為中大心痛
不被玷污的勇氣
低谷、幽暗與希冀
活出真誠
應付假消息的三種方法
在聆聽比說話更重要的年代
學生會的興衰
愛國等於愛黨的荒謬
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亂世中應留守或離去?
香港真係好靚
蘋果日報的脊梁
北京奧運與東京奧運
流亡者的憂慮
記與余英時先生的一次相聚
重聚
公民社會的興衰
在黑暗中看見彼此
當石牆沒有花
二○二一香港家書──天光多傷痛挫折 亦盡力生存
在荒謬的時代,如何面對無力和恐懼
當行之事 活出歷史
當年團友 今天政助
牆內外的人
再見英女皇
北京四橋示威勇士如何動搖中共管治威信?
白紙運動
中國人的紅色藥丸
二○二二香港家書──頑石從未成金 仍願場上留足印
你要學會的,是等待自己
檔案編號NSD RN 20000013
家與心房
<作者簡介>
羅冠聰
香港民主運動領袖,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目前流亡海外,居住在英國倫敦。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是參與政府對話、辯論政治改革的五名代表之一。2016年,他與黃之鋒等人創立「香港眾志」,並投入香港立法會選舉,以23歲之齡當選為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但事後遭取消資格。2017年他因參與雨傘運動而入獄,引發全球各界對香港人權和民主運動的關注。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前夕,他離開香港,展開流亡生涯,並持續在國際上為香港人發聲。他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並在2020年獲選《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
★內文試閱:
•推薦序
時代推著他前行,他亦推著時代前行
桑普(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
記得上兩次同羅冠聰見面,一次在倫敦,一次在台北。
去年一月,寒風凜冽,阿聰和朋友們與我相約在倫敦一家粵菜館用餐。久別重逢,敘舊緬懷,淺談近況,心暖情真。阿聰當時提及他即將出發,北上英格蘭、蘇格蘭數個城市,宣傳「香港協會」(HKUC)文化活動,積極充實。六月,羅冠聰來台北演講,暢談大作,座無虛席。經我借鑒,台灣香港協會年輕夥伴們同年舉辦了「香港八月」一系列文化活動,集飲食、市集、演唱、講座、聚會於一身,讓台灣主流社會與香港族群彼此溝通理解,背後其實深受阿聰的熱情及往績感召。我們都分別離開了香港,堅持拒絕遺忘,積極努力,投入社會。這種心境是許多離港人士的深刻印記。
我和羅冠聰相識於「香港眾志」還在香港政壇活躍時。羅冠聰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堪稱時代弄潮兒。後來因宣誓事件被褫奪議席,又因訪問台灣被追打及返回香港後受襲,再因雨傘運動前公民廣場集會案被短暫囚禁,可謂命途多舛。在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的大部分期間,他在耶魯大學進修,但仍積極在國際線上投入貢獻,為香港人權奔走呼告。在二○二○年國安法實施前,阿聰流亡英國。身處海外,阿聰繼續社群工作,曾與時任美國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會面,並且從香港政治人物轉型為對抗中共的國際倡議人士。
阿聰出身寒微,性格內向,但勤奮認真,不平則鳴。回想當年,我傍晚在香港主持直播電台節目,偶有致電訪問阿聰,他大多對答如流,言之有物。遇到戴耀廷教授向我談及某些政治策略上的創新想法,我也曾約阿聰出來單獨討論。他談吐穩重成熟,進退有度,令我印象深刻。
我認為這本書特別精彩的一篇文章叫〈家與心房〉,壓在最後,但很值得讀者優先閱讀。文章透露了阿聰與父母之間的糾結與距離、愛與恨往往牽扯難分、命與運往往可即可離、人與人之間的愛不是理所當然、阿聰究竟如何渡過童年等。對照目前港共專政集團對身處海外的阿聰通緝懸紅、對阿聰的家人及前夥伴在香港騷擾恐嚇,更見阿聰立志之堅、出泥不染之稀、中共作惡之深。
羅冠聰不在香港出生,沒有親歷自由繁榮的港英年代。一九九九年,他隨母親從深圳來到香港,與父親團聚,先後在屯門大興邨、東涌逸東邨居住,家境清貧,溫暖或缺。阿聰就讀東涌的教聯會黃楚標中學,是深紅「愛國」學校。書中談到阿聰參加學校的七天北京交流考察團,以及有機會被「揀卒面試」進入「灰線」組織這段「機遇」,猶如在鬼門關前掠過。然而,正是這樣的人,坦承剖白,自覺覺他,數年之後感召了很多香港人爭民主、要自治、反專制。當中有「時代推著他前行」的部分,也有「他推著時代前行」的部分。當中出現的人生轉折及心路歷程,尤其是二○一九年至二○二三年這段期間,從挫折、負笈、回港、流亡到政庇,他究竟是如何面對的?很多細節,留待讀者,通讀全書,仔細琢磨。
接下來,我想從更宏觀的角度,談談一些更深入的看法。當中部分觀點,或會引起爭議,盼未來與同道們進一步交流切磋。
一、 去留
首先,書中提及「離去」與「留下」這個二擇一的艱難決定。羅冠聰引用譚嗣同的「去留肝膽兩崑崙」來說明兩個選擇各有其道理。當然,這是正確的,而且每人都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奮發生活。我以下僅集中談「離去」。
畢竟,面對馬克思加秦始皇的中共極權暴政,我與羅冠聰都選擇了「離去」。我們有遺憾,但無後悔。我離港前在電台節目公開講過:「二○二○年的香港就是一九四九年的中國,要選擇做巴金、陳寅恪,抑或選擇做胡適、傅斯年,現在就是生死抉擇時刻。」當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今已逐步應驗。君不見前車之鑒,有些同道好友滿腔熱血,本欲離而未得,終致身陷囹圄,教人痛心疾首。屈原《哀郢》有謂:「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鳥飛返故居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此言甚是。畢竟斷捨離知易行難,雖然無法「忘」掉香港,但也必須快狠準。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以理性、史識、經驗、常識,克服懦弱、惰性、自欺、迷戀,是抉擇的關鍵因素。抉擇後,忘不了,不能忘,也不用忘。
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講過:「哪裡有自由,哪裡是吾國。」(Where liberty dwells, there is my country.)余英時改蘇軾詩贈高行健:「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已破天荒。」這些都不是信口開河,而是背後有一套整全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在基督信仰的基本觀念中,人生在世就是「流寓」,因為人與神的關係不因地域、種族、國家而異。儘管我們既有「家」,也有「國」,有義務盡忠效力,但我們有選擇離開專制極權險地、困地、極地的權利,以及選擇「落地生根」並發憤效忠自由國家的自由。英國清教徒乘五月花號移居美國,愛因斯坦離德赴美,都是正確的決定,影響後世至深。胡蘭成與周作人,胡適與冰心,去留殊途,生死永隔。梁啟超《去國行》有謂:「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為功。我來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聾。」這或許反映了我和羅冠聰的心跡。離開了的人,謙卑努力不懶惰;留下來的人,適時反抗不合作。不要死,好好活,準備好,等運到,光明始終會到來。
二、罪咎
離開了的年輕手足們,大多充滿著罪咎感:捨離坐牢同伴、乍聞同伴噩耗、光復志業未竟、精神肉體創傷、前途茫然空白、人生計畫重置、親友愛情變質、新生適應困難、難忘香港一切。當人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深刻轉折,這種罪咎感,揉雜著鄉愁,勢必降臨。然而,我們必須懂得克服這種罪咎感和鄉愁,因為它們只會帶我們回到「過去」的時空記憶膠囊,並堵塞住朝向「未來」樂觀、積極、夢想、勇敢、創新、試驗的康莊大道。從今以後,就讓罪咎感和鄉愁殘留在腦中一個微小角落,不要讓它們噴湧至遮天蔽日。這是包括我和羅冠聰在內很多人士的日常功課。
正是這種濃得化不開的罪咎感,結合著流亡者海外逐漸膨脹的金錢權力自利野心,主導著部分「中國」流亡海外民運人士的命運,產生了各式各樣的離地與異化,足足延續了至少三十多年。香港流亡人士應引以為鑒,不應單純以一句「中港殊途」作結,因為人性畢竟是共通的。對於這種現象,經歷過文革浩劫的哈金論述流亡的作品,很值得大家品味。哈金寫道:「如果你走出國門,你就不得不像別人一樣正常生活:以個人的勞動來支持自己和家人,靠自己的能力與別人競爭,興敗存亡全憑一己之力和運氣。這種平等是自由的起點,既折磨人也是機遇。」「他們渴望某天能夠回歸自己的故土,這種懷舊心情往往剝奪了他們的方向感,並阻止他們在任何一個地方落地生根。」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也講過:「人生下來不是為了拖著鎖鏈,而是為了展開雙翼。」這些話語,盼與大家共勉。
三、身分
我知道時至今日有很多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經常討論「身分認同」的問題,歸根結柢是想不斷反覆地確定、提醒、表示自己依然是「香港人」,結聚同質者,覺得這樣才算莫忘初衷。其實,這種想法是把「努力光復香港」與「香港人」劃上恆等號,認為只有「香港人」才會真心「努力光復香港」。我不作如是觀。反共、抗中、復港,其實跟閣下是否 「香港人」沒有必然關係。辛亥革命的資助者、實行者,很多都不是漢人或華人。美國獨立戰爭更是適例。由此可見,「恆等號」無助結成更廣闊和更平等的大聯盟。
一個人的「身分認同」選擇,應以「落地生根」為標準,不應以「莫忘初衷」為根據,否則就會必然發生哈金上述提到的「方向感失序」問題。我兩年前已經說過:我是台灣人,也是勉強可稱為「離散」的香港人,但我熱愛台灣,會把台灣國家興亡放在首位,落地生根,貢獻社會,同時也不會忘記香港,並且與同道們共同努力實現光復香港之路。我認為這種想法與台灣國家利益沒有根本矛盾,沒有魚與熊掌的問題。這樣的我,不會有上述「方向感失序」問題。當然,我無法強制別人接受我這套想法,只希望成為彼此溝通及反思的參考。面對現實,大家不妨參考已經入籍英、美、加、法、德、日、澳、紐、台各國多年的港裔移民身分認同轉變,可謂發人深省。我們從來不應著眼於「過去」和「未來」自己的身分如何,實應掌握「現在」的生存環境,追求落地生根,不求落葉歸根。未來的身分認同,是未來的事,不是現在「預斷」未來必須如何的事。只要我們追求自由與夢想的意志、信念、言論、行動常青,「身分認同」不應成為其障礙。
四、主權
據我理解,羅冠聰思想觀念比較左傾,行文中也偶有「正反合」等辯證用語。此外,阿聰至今沒有清晰主張過「香港獨立」。他追求的是自由、自治、民主、法治的香港,追求香港不成為中國或中共的附庸,亦即他並未排除「光復」開明版「一國兩制」:所謂「真正」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恕我直言,對於這些想法,我未必認同,但無損我對他勇氣、熱情、反抗、寬容、冒險等特質的讚美。
我認為:專制的中國容不下民主的香港。民主的大一統中國也容不下自治的香港。當中國分裂了,香港也會隨之而脫離。時至今日,還把「開明版一國兩制」列為選項,顯然在邏輯與常識方面完全說不通。換言之,中國不民主,一國兩制會死;中國民主了,一國兩制也會死;中國分裂了,一國兩制就不必要了。
香港從小的教育,告訴我們法治、人權、民主、自由的重要性,但沒有告訴我們:如果沒有自己的主權、國家、軍隊保障,那麼法治、人權、民主、自由就猶如鏡花水月一哄而散,也猶如一個細胞沒有細胞壁或細胞膜保護,頓成漿糊。君不見台灣命運之所以異於香港,關鍵在於國家主權、軍隊國防、外交實力,從而危而不危,尤須慎防內滲。
香港人如不追求國家主權,亦即香港獨立,還幻想夏桀老死、商紂從良、文王降世、文景之治,然後光復一國兩制,那就是依然故我心甘情願接受中國有權殖民奴役香港的奴隸心態。奴隸心態不變,二千年來盡醬缸。至於坊間所謂歸英論,更是夢囈,英國笑,全球鄙。何不精誠團結,追求香港獨立?這當然有時機問題,目前不宜躁進,但要準備好我們的政治理想與目標。猶如北斗,定舵前行,此其時也。
三大目標:中共倒台、中國解體、香港獨立。三者缺一不可。當然,世界上沒有任何自由國家政府,在事成之前,會公開支持「中國解體」(或任何國家解體)、「香港獨立」(或任何國家其中一部分獨立)的。所以,中國解體、香港獨立,在國際公開場合,註定是一條孤單寡助的艱難道路,也不可能成為當前「國際線」的主軸。然而,三大目標的重點或樞紐在於「中共倒台」:一旦出現,中國解體、香港獨立的成功契機,就會出現難以言喻的漣漪效應,至少有機會俾便逐一實現。屆時中國解體、香港獨立的秩序與品質,端視各方有識之士及公民社會目前是否準備就緒,伺機而動,一觸即發。中共政權最怕的就是這一點,因為一旦成真,就會連中共倒台後「中國版普丁」大一統專政復辟金蟬脫殼的機會都沒有。不過,我不看好中國人目前的公民意識和觀念文化,但卻看好香港人目前仍正勉力維繫公民意識和文明觀念。因此,這種反差情況相當弔詭,局勢還需要詳細琢磨及沙盤推演。但無論如何,三大目標是唯一出路,需要盡早認真準備。
我衷心期待羅冠聰支持上述想法,或至少不反對上述想法。未來可望求同存異,與全球同道們凝聚更廣泛共識。
五、行動
今年六月,資深評論人練乙錚先生在「日本香港民主峰會」上,發表〈論港獨的知行合一:困境下的獨白〉文章,論述清晰,發人深省,擲地有聲。
練文的重點在於「光復三實踐」:做服務工作(生活、文化、政治紀念)及國際倡議(保護港人、制裁共官)的人力物力,宜大幅轉移到加強對中共及港共政權的直接攻擊力,達到大約四比六的比例。練文所謂「直接攻擊」的例子,包括揭露中共在外國的秘密警察局、反消息封鎖的拆牆運動、向外國暴露中國真相的大翻譯運動等。以上都只是練乙錚先生的初步意見。
這篇文章的意見,正好說出了我的心底話。世界各地同道在過去四年的工作,大體上包括以下六項:紀念、社群、倡議、救援、媒體、營生。不過,我在去年及今年於美加演講時,提出多兩項:光復目標及綱領、組織與行動。這恰好類近練文的重點。我認為:光復目標及綱領、組織與行動,是有志於光復香港人士,今後應該努力的方向。由下而上,加強信任,不宜冒進,逐步醞釀。與其在現階段急於建立任何形式的大台,不如各人先從「對中共及港共政權的直接攻擊力」的「事功」或「實績」出發,或從舉辦深度討論的本國或跨國論壇峰會著手(可以是部分公開、部分非公開),可能是當前更值得實踐的方向。
特此期待包括羅冠聰在內的好友同道們都能求同存異,加強溝通,共襄盛舉。順祝羅冠聰大作《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一紙風行。
•摘文
一、兩道閘門
二○二○年六月中,我一直在不同的安全屋轉移。
三個月前,中共明目張膽表示會繞過香港所有諮詢和立法程序,直接實施港版《國家安全法》(即《港區國安法》)。二○二○年初,因應疫情轉趨嚴重,香港政府禁止市民於日常聚集,同時亦將此緊急權力用於壓制市民集會權利。在疫情和「限聚令」的雙重打擊下,香港抗爭日漸息微,市民亦將重心放在抗疫工程。狼子野心的中共嗅到扼殺香港公民社會的絕佳時機,便順勢在短時間內推出嚴刑峻法,確保香港政府及國家機器擁有幾乎可任意將抗爭者治罪的「口袋法」,撲滅任何示威的火苗,一勞永逸。
於是,《港區國安法》被提上日程,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甚至曾向傳媒表示,她在《港區國安法》細則公布前也與其餘香港市民一樣並不知道詳情。一個完全顛覆香港普通法傳統的法例,就在所有人都被蒙在鼓裡時,猶如聖旨般降臨我城。
《港區國安法》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公布,當時所有活躍的政治組織者都感到如臨大敵,前路相當迷茫。到底這只是一個備而不用的「尚方寶劍」?或是會滲透到日常生活所有角落、猶如中國大陸濫用「煽動顛覆國家」罪名一樣,將所有批評政府的聲音關進大牢?從歷史得知,《港區國安法》是屬於後者,用以消滅反對聲音達致「社會和諧」的積極手段。但在《港區國安法》公布前夕,未知和不安籠罩香港,我們也不禁猜測,當《港區國安法》正式頒布時,所有香港政運人士會不會突如其來被「一網打盡」,甚或立刻送中。
因此,在整個六月,我就已經對個人安全狀況相當警惕,也開始轉換居住地點,避開潛在的監視。驟眼看來,這或許有點使人覺得我像驚弓之鳥,畢竟事後也知道政府的拘捕行動不如預料般電光火石;但他們企圖將香港反抗勢力一網打盡的野心,還是能在事後以不同案件大規模搜捕香港民主派一窺究竟。
距離六月三十日公布《港區國安法》尚有兩個星期,此時我大約已經知道,我會在六月底離開香港,也許這是一條「不歸路」──但這個決定並不能帶來解脫的感覺。一來曾有離境者被機場海關攔截的案例,我或早已在政府的黑名單中,因個人的政治立場而被限制出境;二來就此離開一個我曾立志為它的未來和自由奮鬥的城市,心有不甘,亦對未來感到徬徨。離開了香港,我仍可如預想般繼續為它發聲嗎?香港的支持者和市民,又會不會反對這個離開香港的決定,認為這是對理想的背叛?
在離港前夕,夾雜著思想上的渾沌以及對人身安全的擔憂,我不斷穿梭在港九新界的每一個角落,看著香港都市繁華、小城冷清的每一幀畫面,不由得衍生出千種感覺。我在思想和情感上超出負荷,使我日漸感到疲累之餘,也有更強烈的末日感。
那段時間,仍是二○二○年民主派初選的宣傳時期。我預計一旦未來被香港政府通緝,知悉我離港決定的人或會惹上官非,被指控協助我離開香港。因此基於安全考慮,我並沒有與團隊、家人商量,內心藏著一個大秘密,但又貌似如常地過活。
這並不容易,也並不好受。
那段時間,我特意相約很多熟悉的好友見面聚餐。雖然香港與外地的交通非常方便,但有些好友被捕後旅遊證件被沒收;當時也正值疫情,尚未開放,在海外相見也不容易。我與他們聚首時,便暗暗感嘆不知何日再見。
六月二十五日,我最後一次離開在東涌的家。那是一頓很漫長,又很快速的晚飯。內心的糾結影響了時間的流逝,使它變得絕對主觀;理性和感性對現實的詮釋被不安和不捨打亂,我想留住眼前一刻,奈何卻深明時間終將向前。我仔細地觀察餐桌上的一切,卻又非常清楚,我最好快一點忘掉。
由於我早已與家人分開居住,不時都會帶來行李箱出入,在享用過晚飯後,我徐徐收拾行囊,準備起行。當時擔憂在機場可能會被海關或警察攔下,因此我將所有電子儀器都清乾淨,只帶了一個背包以及手提行李箱,盡量輕裝上陣,減省它們被沒收時的麻煩。
眾志的年宵外套、監獄的書信、幾件替換衣物……很多富有紀念價值的物品,包括立法會議員時期的文件、《青春無悔過書》贏得的書獎等等,都要被遺留在家,等待一位不會回來的主人。
之後我重新回到安全屋,收拾好心情,等待出發的日子。
我記得那天起來,就好像二○一七年準備上庭迎接公民廣場案判決一樣,周遭事物色彩變得鮮艷,五感特別靈敏。二○一七年上庭前,我們早已知道唯一的判決結果是入獄;二○二○年啟程前往機場前,無論是登上前往倫敦的客機,或是會被拘留在邊境,雖然處境大相逕庭,但對我來說,都是猶如二○一七年般糟糕透頂的結果。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根浮木漂浮在名為香港政治的急流上,在身不由己的客觀環境下,做有限的自主決定。一顆爛橙和一顆爛蘋果擺在眼前,我只能選擇其一,然後接受自己的決定。
戴著一頂漁夫帽,我乘坐計程車來到機場,守在門口的警衛查看了我的登機證後,便讓我通過。當時機場仍實施疫情下的出入限制,只能讓持有效登機證的乘客進入,連飛機接送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務求減少人群聚集。我順利進入機場,意味著我有驚無險地通過了第一個檢測。
航空櫃檯登記,成功通過。從離境大廳進入禁區之間,相隔著檢查香港身分證的電子通道。通道是由兩道閘門組成,將身分證插入機器檢查,驗證成功後取回身分證,第一道閘門會隨之打開,進入後你將被困在兩道閘門之間。設計原意是讓入境處職員以最有效的方式將嫌疑人士拘留,但這道本應只花三十秒的程序,卻成為整個行程中最令人膽戰心驚的章節。
通過第一道閘門後,我需要在機器上驗證指紋。我按著指示將拇指按上,而本應打開的第二道閘門,卻遲遲沒有反應。
三十秒、一分鐘、兩分鐘……沒有反應。
閘門的顯示器沒有任何特別標示,只是要我耐心等待。這段時間裡,我腦海快速模擬了多個可能性:是我的拇指太乾燥導致檢測不良嗎?還是我離境程序觸發了黑名單警報,警察正在火速趕來?或是我的模樣太過可疑,觸發職員的隨機檢查?
缺乏資訊的我表面冷靜,實際額冒冷汗,度過了人生中最慢的幾分鐘。
實際時長我也忘了。那種情況,是不可能冷靜地計算自己等待多久,然後再盤算日後將這個細節寫入書中。
不可能。
當我心急如焚時,第二道閘門打開了。沒有警察,也沒有入境處職員等待著我。我拖著手提行李箱,走到閘門口附近的椅子,面對停機坪、背對走道,靜靜坐下。在二○二○年,由於已有一批批示威者在面對司法程序前嘗試離港,因此機場登機閘門不時有便衣警察巡邏,隨機審問容貌年輕的登機乘客,捉拿那些「漏網之魚」。亦有其他案件,是當飛機在跑道準備起飛時,已順利登機的示威者被警方在機上逮捕,無法離開。因此,即使完成了離境手續,在起飛前我都無法定下心來,只能鎮定地看著跑道上的飛機,幻想著它起飛的一刻。
結果我沒有被盤問,成功登機,坐在乘客相對稀疏的客機上,靠著窗戶,緊緊抓住眼前香港的面貌。飛機滑行,在跑道上加速,機身傾斜,我的視線拔地而起,看著萬家燈火的香港夜景。
這是全世界最美麗的畫面,在我心中無可取代。
飛機穿過雲層,我的眼淚也隨之落下。流亡成為事實,下一站是倫敦。
我又會迎接一個怎樣的人生?我看著眼前的星空,思索著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