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鏈下的未來戰爭:時間、空間與人性的消逝/蔡元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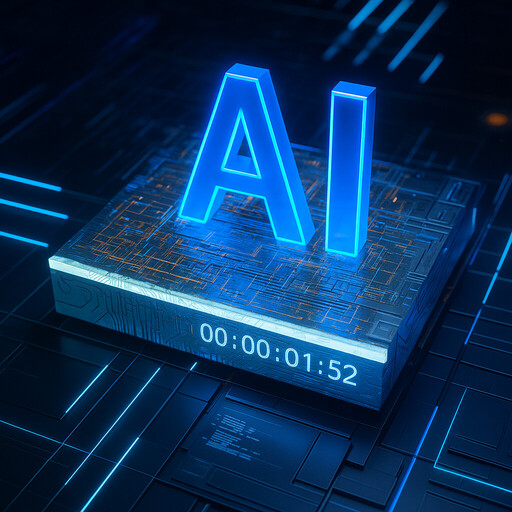
蔡元鴻(軍武科技觀察家)
印巴雙方於5月7日的空戰之後,巴基斯坦展現聯合作戰體系與資訊鏈路的高度整合,與過去單純消耗敵方兵力為衡量標準不同,使現代戰場更強調透過時間、空間與資訊優勢,為己方爭取更長的戰略緩衝與更有利的外交籌碼。然而,當人工智慧(AI)與各式無人載具全面融入聯合作戰,這場「數據驅動的角力」,將進一步放大人性的消失、決策節奏的加速,以及不對稱手段運用的殘酷與無情。
首先,傳統戰爭往往以擊毀、奪佔敵方有生力量之數來衡量勝負,但在聯合作戰與C4ISR(指揮、控制、通訊、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網路高度整合的今日,一場作戰若能透過秒/分鐘級的資訊傳遞,提前干擾或瓦解敵方部署,就已相當於獲得「時間優勢」,迫使對手重整陣腳,為己方創造寶貴的重整窗口。與此同時,傳統地圖上的「空間縱深」將被電子戰與網路攻防替代:在關鍵節點封鎖敵方資訊流,例如利用電子干擾癱瘓對方雷達網路,或透過網路攻擊擾亂其後勤系統,即使沒有大量擊毀硬體設施,也能讓敵方在戰術與後勤體系上陷入混亂,進而打擊其持續作戰能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在某次行動中成功滲透或截獲敵方指揮系統的重要情報,對手就不得不在戰後談判時,顧慮自身軍事行動計畫已被看透,這種「資訊透視+心理嚇阻」,遠比純粹的物理破壞更能轉化為談判籌碼:無論是爭取更長的停火時限、交換俘虜的有利條件,還是改變戰後重建的議題,都可能成為衡量勝利的新標準。
其次,未來在多領域聯合作戰中,AI將成為聯結空中、海上、地面、電磁與太空等領域的核心樞紐。透過衛星偵察、無人機影像、電磁截獲等各類感測資訊,AI演算法能在毫秒內篩選並分級威脅,直接向無人載具下達攻擊命令,讓原本需「人腦審查—上級批准—打擊執行」的流程大幅縮減,幾乎達到「零延遲」的決策速度。
雖然可提高反應效率,卻大幅降低人性化的制衡:若AI系統只是根據預設算法,將一個疑似目標直接標註為敵方高價值目標並下令攻擊,即便只出現極小誤判,也可能瞬間造成重大誤傷,而人類擔任的指揮官根本無暇介入。與此同時,前線與後方的界限也因為UAS(空中無人機)、UGV(地面無人車)與USV(海上無人艇)等平台的無所不在,而逐漸模糊。這些無人載具沒有求生意識,只會依照AI指令不斷接近並壓制敵方,讓敵方在撤退或掩蔽時的生存空間被徹底壓縮。
更甚者,當「損失一架無人機」只被視作純粹的物資補給問題,且能迅速替換,指揮官更願意冒險發動高風險滲透或擾亂行動,因為損失的只是一連串「數字」,而非具名人員的生命;這種去人性化的損失成本計算,使得戰爭成本更加冷酷。同時,大規模自治無人載具編隊所帶來的「數位恐懼」,對手一旦明白對方能全天候監控,並在毫秒內下達消滅命令,就會承受極大心理壓力,若稍有閃失與遲疑,就可能在瞬間被瓦解,因而進一步助長先發制人的慾望,使得戰場變得更為無情殘酷。
再者,面對AI與無人載具的快速發展,國際規範往往落後於技術進步。儘管國際社會已多次倡議禁止自主致命武器系統(LAWS),但各國在技術研發與部署上仍走在法規之前,認為只要能在戰略層面換取更大的緩衝與籌碼,即使可能違反國際人道法,也在所不惜。這種「技術先行、法規落後」的現象,將使得戰爭門檻進一步降低。
另外,AI取代人類判斷,無人載具替代有人作戰,將使人性中的憐憫與道德制衡降低。若缺乏對AI決策過程的透明,以及足夠的可追溯性,誤判發生時人類難以即時介入,戰後追責也將變得愈發困難,進而進一步放大戰爭的殘酷程度。更重要的是,在AI驅動的先發制人攻擊,與無人載具全球化部署之下,傳統「前線」與「後方」的概念逐漸消失,戰爭形態由區域性對抗轉向「跨領域、跨時間」的全天候對決,許多衝突的起源,在國內尚未充分審議就已觸發,令國際社會更難釐清正當防衛與侵略之間的界線。
未來戰場將比一戰、二戰,甚至俄烏衝突更為殘酷無情,沒有太多餘地讓人性稍作停留,也無法指望國際規範能即時補位。時間與空間的壓縮、資訊與AI的加速,已經讓殺戮成為一場數位演算,只要滿足「最小誤差、最高效率」、即可秒下殺戮令;無人載具的無所不在,更使每一名作戰參與者都成為目標。當自身或對手的失利只被視為可快速替換的「數字」時,任何同情與憐憫都變得奢侈。技術的突飛猛進與人性的遲滯,讓這場競賽更加殘酷:沒有人能保證哪一方能立足到最後,也無法依賴悲憫與理性將其遏止。未來的衝突,以其無情和迅猛的特質,將進一步顛覆我們對戰爭的想像,也提醒所有人,未來或將無勝利者,只有生存者。(照片示意圖翻攝畫面)
- 記者:好報 採訪中心
- 更多生活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