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之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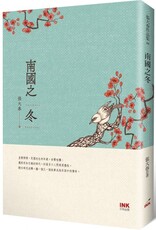

南國之冬
作者:張大春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1-03-05 00:00:00
●「春夏秋冬」系列最終回,歷時十餘年磅?面世!
皇朝將傾、民國初生的年歲,世聲喧騰;
龐然有如巨幟的時代,抖落多少人間瑣屑塵埃。
隨任時光流轉,
讓一個又一個故事成為耳語中的傳奇。
「你總也要幫忙人找丟失的東西的。」
「你丟了什麼?」
「故事。」
傳說得著人間藏王祕傳的銅缽,便須替他人尋回失物。
但一切該從何說起?是宮寶森師兄弟的生死流轉?還是名導胡金銓齎志以?未曾完成的電影?還是清末民初世事裂變中風起雲湧的豪傑兒女?還是……還是……?一個接一個故事,如連環套一般層層疊扣,復又相互推衍,終而令人迷眩在首尾相銜、無終無始的迴圈裡。
迴圈的原點本是為了一齣戲。藉由追索葉問遺留在歷史上的殘痕瑣跡,以電影還原「一個時代的真實角落和確切面貌」。然而層出不窮的故人軼事彼此連綿交織,乃至歧杈蔓衍,讓人分不清究竟是故事、還是現實?
張大春以文字展現逐漸為人遺忘的小說家本質──搬演、播弄故事的說書人。在《南國之冬》裡他再次掇拾掌故,彌縫虛實,鋪演百餘年前的民國創生史,細數龐大時代浪濤中的無數傳奇。
在他筆下,戲裡的傳說野史從不曾於戲外止步。於是,無論說書的還是演戲的,那些劇中的故事又豈止是「故事」而已?而對那看戲的或是看電影的,日後供人圍看的也未必只是他人的人生。
★內文試閱:
楔子 畢順風
歷來講古道故,都有個引子,正話不及宛轉而說,先扯個閒篇。當年在瓦舍裡,這叫「得勝頭回」,取其開張大吉之意。此時不能壞此規矩;遂也說一個得勝頭回,拈出《南國之冬》全篇線索,猶如鬼神故事裡經常聞見之「血餌」是也──粗觀之,一個不辨真偽、全無干係的偏遠故事,更與史事現實,了不相涉。用說書人經常打的譬喻來說,不外是草蛇灰線,未睹形影;細思之,將這得勝頭回置諸全書之間,竟也首尾無缺,因果俱全。且一小小榫合機關,居然照應全篇,為千百人物事端的發軔,這也是後世風聞熱鬧之人,於可喜可愕之際,所不能追勘覆按者。
正是──
河南嵩陽有個出了名兒的人,叫畢順風。給叫畢順風,有許多緣故,其一是因為他少年老成,比旁人活得都快。畢順風少年老成,半是因為長相,年紀才剛上十五、六,一頭黑髮就漸漸花白了。人過二十,得了一場大病,猛裡瘦下來,痊可之後,滿臉的皺紋捏出一張垮臉,人都當他七老八十了。這樣的長相未必沒好處,出門做生意,人都看他年長輩高,凡事敬讓三分。至於東西周轉、南北流通,幾多年下來,生意越做越大,他還是一副腰腳頑健的模樣,外人不知他其實還是個少壯,更聽不出他鄉音里籍,只是尊仰他年事老大而已。
這還不算,成天價出門在外,什麼人會須應付?什麼人必須疏遠?什麼人可通款曲?什麼人可共福禍?這都得察言觀色。一旦在這一層上做得工夫,聽人說話就不吃力了,仰體意旨,曲意逢迎,往往窺得人心機於無形之間,讓人無從提防;總感覺同他相處十分融洽,不論談什麼,他都能順絲就理兒地捧著話題奉陪到底,何如一江春水向東流,直掛雲帆濟滄海?號之曰「順風」,還覺委屈他了。
這回說畢順風,是因為他老婆懷孕了。夫妻倆結褵三五載生兒育女,原本極是平常。可畢順風不常在家,年近三十能添子嗣,自然萬分欣喜,算計著產期近了,就急急忙忙往家趕。不意於離家五十里上錯過了一個宿頭,又走了一、二十里才感覺困乏,想起來了,已經無處可以打尖。只得在一爿破廟裡將歇了個把時辰,拿出包裹裡的乾糧來充充饑,皮囊裡還有一斤多的白酒,使小錫碗盛了,咂巴幾口,精神過來了,又急著回家照看妻子,不覺動了個趕夜路的念頭──還有三十里步程,到家不過天剛大亮,搶搶路,怎麼樣也不至於錯過妻子的產期。於是一咬牙、一跺腳,鼓著勁兒上路了。
才過那破廟不過二、三里之遙,便見前頭一個婦人低頭疾走,那婦人裹著小腳踩著蹻,步伐卻快得驚人。畢順風想:自己一個人走,容易疲累貪懶,索性跟著那婦人的腳程,一鼓作氣地走下去,說不定還早到家了。主意既定,緊跟著婦人又走出一里地去,才發覺一樁怪事:這婦人走了這麼大半天,居然沒有鼻息動靜,腳下也不見祟動。若非內家功夫練得極高,就是妖鬼之流了。畢順風不覺打了個寒顫,正想開口問訊,那婦人卻回過臉來,微微一笑,道:「老人家如此趕夜路,不叫辛苦?」
畢順風慣給人叫老,自然不以為意,順著話說:「夜裡不睡晝裡睡,這是咱們上了年紀的習以為常之事;小娘子莫怪。」
「不過,」婦人撇過臉來,朝他腳下眄了一眼,道:「老人家腳程卻是不慢。」
原本一腔家有喜事的欣然,衝口就想說:「我老婆在家要生了。」可畢竟還是心機用多,真情慢吐,畢順風一嚥唾沫,把滿心樂事吞回肚裡,只道:「生意浪裡飄滾浮沉,全靠腿子勤勵,慣走快了的──可等閒還及不上小娘子。」
「你跟我比?老人家,怕你比不得哪!」婦人又笑笑,倒像是也有什麼掩藏不了的喜事要說,一時也忍住了。
畢順風趁她回頭之際,從背後仔細一打量,才發現那婦人的一雙三寸金蓮根本不沾地兒──換言之:她是飄著向前走的。不消說,是個鬼。夜行荒野之地,撞上個鬼,常人該當如何?說書的不知道。可咱們畢順風生意浪裡飄滾浮沉慣了,撞上什麼東西沒有一套應對進退之術呢?便先跟著打哈哈:「一副老骨頭勉強湊附著,眼見就要拆架了,是比不得小娘子青春。」
「我也不瞞你老人家,」婦人依舊笑笑,低聲道:「諒你老人家見多識廣,必有些兒膽識,經得起──我不是常人,是個鬼。」
「嗚呼呼呀!老朽夜路走得夠多,也要到了這把年紀,才能見識一回。」畢順風假作新奇難得之態,細細觀看,嘖嘖連聲,接著道:「小娘子年華正好,怎麼就做了鬼,真是可惜!」
「真要論起歲數來,我也是應該做婆的人──只因十八年前產子血崩而死,蹉跎到今,還不得投胎。」
原來是個「產鬼」。畢順風聞言心下不免大驚。早就聽村里間的耆老說過:產婦臨盆,要擔十分風險;若有什麼三長兩短,到了閻王爺面前還得擔十分罪過──因為這樣死,是絕人後嗣的事,容或此婦生前在三從四德上沒有一絲過犯,到頭來禍起臨盆,往往不能順利超生,於是就有了「討替」之說。
什麼是「討替」呢?就是再去找一個即將臨盆的婦人,讓那孕婦不能順利產下嬰兒,也和自己一樣,死於產程之中。倘或耆老們的說法屬實,這婦人急慌慌前去「討替」的對象,不正是自己的老婆嗎?畢順風越是心驚,越是不敢露出半點兒顏色,反倒拱起手來,連連向那產鬼作揖:「真是得恭喜恭喜了!小娘子這一十八年等替,得多麼艱難?老朽孤身一人,向未婚娶,不知此中緣故,可一向聞聽人說,生兒育女要擔萬分辛苦、受萬分風險,如此尋替應該不難罷?」
「難呀難!老人家,你有所不知──」產鬼的腳步慢了下來,雖然說起辛苦,眉頭不免要皺,嘴角還是忍不住浮露著淺淺的笑意:「陰曹有一本帳,總要將生平善惡加加減減,以平得失、均果報,一身的罪孽贖滿了,才許『討替』。十年前我原本可以上南省裡某縣向一個婦人討了,無奈去至彼地,才知道那婦人修佛持戒了幾年,等閒討她不得。」
「之後就再也沒有可討可替的婦人了麼?」畢順風捋著鬍子說,「那麼這今世的婦人倒也是德行圓滿的多。」
「倒也未必。」產鬼難得一見這麼個擅長聽話的,真像是憋了十幾年未嘗對人開口道故的一般,遂靠著路旁大青石坐了,道:「婦人持家,單是殺雞宰鴨就積累不少血債,說什麼德行圓滿,倒也未必。就怕是那些個原本該入山清修的老道,經常到處逡巡。他們的邪術太多,總是對付咱們這些苦命人。一朝口耳相傳,家家戶戶都會通些個不教咱們親近內宅的方子,那才惱人呢。」
「鄉里間的道士素行狡獪,人都說道士比妖鬼還難纏。鬼還怕陰司盤算,道士是什麼都不怕的。小娘子也吃過道士的虧不?」
「說起這就一言難盡了。」產鬼歎口氣,道:「十年來我年年可以討替,卻總會遇上此輩,他們不過是為了換幾頓血食,便將許多天人祕法悉數傳授給滿世界的愚夫愚婦了!」
「我是個生意人,生意人將本求利,只問出入划算與否。你既然是死於臨盆血崩,必然也是為產鬼討替作祟,這裡頭就有本利出入的計較了。試想:人討了你一命來替,終不至於教你沒處可討以替之罷?倘若那些個搖串鈴兒、走江湖的道士們任意施作祕法,他們欠的帳,該誰討去?」畢順風順風說話慣了,這一串言語根本是毫無根據的歪纏,可聽在產鬼的耳朵裡,直似是替自己鳴不平,猛地樂了,產鬼拍手笑道:
「就是這一說!就是這一說!我就說生意人公正明白,天上地下人間,哪兒都得要多些公正明白人才好!」
「可有一樁我外行,不明白,」畢順風道,「討替總得有個作為罷?你都是怎麼討、怎麼替呢?」
「別說你不明白,我也是做了產鬼才明白的。」產鬼點點頭,笑著一昂下巴頦兒,露出了脖梗正當央一個紅豆大小的圓點,道:「老人家!我知你身上有酒,你且含上一口,見我這廂手一拉扯,便將酒噀過來。」
產鬼等他把酒含住,作勢扯喉間紅點往外一拉,看似什麼也沒拉出來,可是當畢順風的一口酒沫子「噗喳」一聲噴上去──看見了!從產鬼的喉頭直到指尖,酒霧之中隱隱約約看得出來,一條顏色赤紅、似絲又似血的細線。待酒霧漸散,紅線也隱沒了。
「這,是個什麼戲法兒?」
「這叫『血餌』。」產鬼說:「將此物縋入產婦口中,它自會去尋找嬰包,找著了嬰包,我這廂便渾如釣魚的一般,緊緊扯住,不教那嬰包墜下;復暗中用力抽掣,保管那孕婦痛徹心肺,三抽五抽下來,娘兒兩條命便都葬送了。」
「你一十八年辛苦等待,總算也熬出頭了不是?」畢順風將綴在酒囊旁邊的小錫碗取下來,倒了一杯,向產鬼遞過去:「得以超生終是大喜!老朽一定要敬小娘子一杯。」
產鬼也不辭讓,捉起小錫碗來,放在鼻孔底下猛可一吸,旋即飲空了,產鬼的臉也紅了,但是說起話來,聲音忽然多了幾分愉悅:「多謝老人家賞賜!回思這十八年來,日夜盼想,朝暮牽掛,還不就是成就這一樁討替;眼看這一二日便要成事,之後呢,雖說大約還是投胎做人,想來久不為人,還真有些不慣呢。」
「老朽行年七十,奔波一世,見多了一時得意、因而毀棄一世功果的事。古人說得好:『行百里者半九十』、『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越是功德將近圓滿,越是要加意防患,不要橫生枝節才是。」
「這我卻不擔心。」產鬼擎過杯來,像是又要討酒喝,畢順風給滿滿斟上,聽她繼續說道:「今番要去的嵩陽畢家那男人出門在外,產婦孤身在家,極好下手的。」
「老朽除了生意經、還是生意經──看起來你們產鬼這一行也是做得,」畢順風笑道,「就算撞上吃齋念佛的信女,討不了替,也蝕不了什麼本錢,並無風險。」
「話不能這麼說,老人家!風險何處沒有啊?」產鬼端起小錫碗,使勁下鼻一吸,又喝了個乾淨,看情狀還是要討,畢順風豈不捨得,連忙再斟上,聽她又說將下去:「我看老人家是忠厚長者,倒可以給老人家解解惑──你可千萬別出去抖露,那我們做產鬼的就更辛苦了。」
「我也是行將做鬼之人了,小娘子!你說說看:就憑我這德性,是同你們結交為伍來得上算呢,還是同那些後生們結交為伍來得上算呢?」畢順風一面說,一面假意經不得夜風吹拂的模樣,嗆聲大咳起來。
產鬼一聽這話,更開懷笑了,道:「老人家真是快人快語!快人快語!我也不瞞你說了,產鬼還是有絕大忌諱──咱們最怕的就是傘!尋常人家只需將雨傘置於門後,我們就進不了宅屋。這也是一等十八年、還縋不到一條替命的緣故。」
「照你這麼說,這行當可還怎麼做?」畢順風猛搖起頭來,「家家戶戶都有傘,為了出入取置方便,自然都是放在門後。教你這麼一忌諱,我看別說人家那姓畢的男丁回不回來,他就是已經橫死在外頭,你也討不成替的了!」
「不不不!討得成,討得成!我這十八年孤魂野鬼也不是白做的──有個老產鬼,教過我一門身法,說是家家戶戶當初起造房宅,落成之際,都有瓦匠領工勘驗,所謂『探頂子』是也──『探頂子』的時候,多少總會留些個『堂穿』,取其不至於『滿招損』之意。那老產鬼教我的身法,正是藉由這些『堂穿』縋下『血餌』,一樣能取了產婦的性命。」
「既然如此,」畢順風乾脆將那只盛酒的皮囊遞了過去,笑道:「既然如此萬全,就只合在此為你小娘子先慶功了!畢竟投胎轉世是大功果,你喝完這一囊,趕緊上路罷,老朽腳程慢,不敢耽誤你呢!」
誰知那產鬼卻像是鬧起俚戲來了,抓起酒囊湊在鼻子前猛吸了幾口,一面打著嗝兒,望著天邊斜月,說:「咱倆這一聊、一耽擱,看光景,今夜頂多還能再趕個十幾里地,就要天亮了。我白晝裡不能趕路,如今走得再快,也還得到明日前半夜才到得了地頭。索性喝罷了找個地蔭子休息一天,明日再去不遲。老人家,何不也一道喝兩口,歇息歇息再說呢?」
「小娘子到了嵩陽就算功德圓滿,老朽我還有百把里前路要走呢!不然,你看我夜來不宿店,忙和些什麼呢?」畢順風說著起身,又恭恭敬敬朝產鬼作了一個大揖,道:「但盼小娘子奇緣佳會,隨時而致。老朽還得趕死去!趕死去!」一面說著,一面撒開腿便朝前走。
畢順風一到家,產婆已經在屋裡忙和著了,老婆果然是難產。但見這畢順風搶出搶入大半天,上左鄰右舍家張羅了不知幾十把大大小小的傘來,屋前屋後張置遍了。此夕太陽才甩西,產鬼便來了,打從黃昏時分起,便在畢家宅子牆外呼嘯旋繞,時而悲啼,時而怒叱;最後似乎發現了主家翁竟然就是夜來野路之上所遇見的畢順風,更是厲吼村罵,聲嘶不竭。
畢順風的答覆很乾脆,還是生意話:「你這產鬼的行當不成理──顧全你一人投胎,卻要我家賠上兩條性命!哪有這種渾事?」
畢順風一家子暫且逃過一劫,按理說,故事就結在此際。倒是那還來不及出生就撿回一命的孩子,卻另有奇緣。雖曰難產,但是一旦呱呱墜地,求生之意忒不尋常,從小就魁梧健碩,百毒不侵。到了十七歲上,他應省選,成為第一批赴日本成城學校留學的士官生。
這是當時張之洞一力推行的重大育才政策。一批又一批由各地方面大員親自遴選的健兒,跨海求經,以謀國族武力之更新強大,影響近代中國最早的軍事以及政治至巨。首批留日士官生一共四十五人,順利完成實習的有四十名,但是只有三十九人畢業,沒畢業的那漢子就姓畢。身形特別高大壯實,在學期間從不生病,然而,偏就是患了一場小小不言的傷風,打了幾個噴嚏,人就在寢室裡故去了,只脖梗上有個顯著的紅點兒,看得最清楚的,就是睡在他鄰床的姚維藩。此事日後在新軍陣營中沸揚喧闐,茶餘飯後,無口不傳。
辛亥革命發生後,首先響應的就是山西的新軍。管帶姚維藩親自抽點所部五百人組成敢死隊,再派遣其中五十個「選鋒」衝陷撫台衙門,其餘的則攻打旗兵營區。不料一接陣,姚維藩派遣的殺手只隨手開了兩槍,兩發子彈出銃,詭異地命中山西巡撫陸鍾琦和他的兒子陸光熙的脖梗,父子一時斃命。姚維藩不能置信,於俯身驗勘那兩具屍體之時,猛地大喊了一聲:「血餌!」旁人事後問他:「管帶喊了啥呢?」他居然渾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