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變不離其宗”/夏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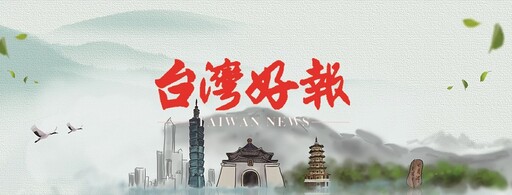
夏俊山
據說,宋代大詞人柳永原名 “柳三變”。此名取自《論語》中的“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父親柳宜給柳永取名“三變”,一是借《論語》中的名句寄託自己對兒子的期望,二是柳永兄弟三人,名字中皆有“三”字,分別是柳三複、柳三接和柳三變,時人稱之為“柳氏三絕”,皆擅長詩文。
我來人間70年,一路風塵一路望,感覺也有“三變”。當然,我的“三變”與《論語》沒有關係,跟柳永八竿子打不著。
我的“三變”,第一變沒啥好說的,就是日復一日在變老。正像尹藝霏演唱的《我們都會老》:“直到銀絲慢慢爬上發梢\發現皺紋也佈滿眼角\老眼昏花了牙齒鬆動了\歲月壓彎了挺直的腰\曾幾何時我們東奔西跑\只想讓生活變得更好\孩子長大了兒女成家了\人生也快要畫上句號……” 變老屬於自然規律,用不著傷感,國王與乞丐一樣,誰都沒有特權。讀《莎士比亞全集》,好像有一句臺詞:“國王與乞丐,在蛆蟲口中不過是味道相同的一道菜。” 年齡增長,時代變遷,我必須接受“世界並不是為你準備的,就算竭盡全力也未必有想要的結果”這種事實。《好了歌》唱道:“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如今的人,最終連“荒塚一堆”都是奢望,大概率都是:化為一縷青煙,一瞬間就飄沒了。
我第二變是:社交的圈子變小了。這並不意味著我做錯了什麼,別人不願意搭理我,也不意味著我認識的人變少了,相反,隨著年齡的增加,我認識的人越來越多,但一起吃飯、聊天、有交往的卻變少了。這一變化,是我在主動做“減法“。人老了,方方面面都應該做“減法”,社交也一樣。人類學教授鄧巴做過研究,社交網路中,我們的精力最多只能維護150個人,而最核心的圈子可能僅有三五人。他曾說過:“到了一定年紀,我們都要學會給自己做減法,特別是給圈子做減法。”老了,“來日方長”變成了“來日無多”,要把時間和精力更多地留給自己,留給最重要的人。
憑藉《2002年的第一場雪》,刀郎一舉成名。音樂圈和娛樂圈卻對他非常不待見,刀郎沒有急著擠進任何一個圈子,甚至都沒有一句解釋。他極其低調,退圈十年。尋找更樸實動人的情感元素。摒除娛樂圈的喧囂與繁雜,他有機會能夠靜下心捕捉靈感,創作音樂。再次歸來時,刀郎帶著新曲《羅刹海市》,火遍全網。刀郎複出給人以啟示:圈子小了,潛心提升自己,可能會贏得更多尊重。其實,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接納孤獨,與之共處,開啟通往內心的旅程,尋找生命的意義,是不會在意圈子變小的,也不會感到孤獨。
我第三變是:辦公室變大了。在海安高級中學教書時,我在語文組辦公室,很多人集體辦公,一個人只有很小的一方空間。退休後,我曾經在海安市煙草局做文字工作,3個人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受聘於興化市文正教育集團,校報編輯部在行政大樓的4樓,是一間獨立的辦公室,電腦、空調、檔櫥等一應俱全,我一個人一間辦公室,上班乘電梯經常遇見集團的領導,董事長也在第四層。有人開玩笑說,你一個人這麼大的辦公面積,假如按國家規定,科級公務員占這麼大面積,已經屬於違規了。可是,儘管辦公室越來越大,我還是感到辦公室太小。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工作方式的變革,遠端辦公、移動辦公等新型辦公模式也逐漸興起,人們可以在更靈活、更廣泛的地點進行工作。我可以在廣闊的天地、大自然中進行辦公。例如2023年暑假,2924年暑假,我分別遊覽了雲南、貴州、新疆,我邊遊覽邊拍照邊寫下文字,發表於《台灣好報》的《騎馬走上茶馬古道》《“藍”動天下的“一滴淚”》,就是在雲南、新疆寫的。遼闊天地間可以辦公,不妨稱之為“天地辦公室”。“天地間辦公”意味著一種自由、開放、無拘無束的工作環境。意味著人可以不受限於固定的辦公場所和時間,而是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環境的變化,隨時隨地進行工作。
孫悟空七十二變,變來變去,最終還是改不了。雷公嘴、滿面毛,身高不滿四尺,腰系虎皮裙,手拿金箍鐵棒的猴兒樣。我這“三變”更是改不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事實。但是,我相信:真正的英雄氣概不敢於在刀光劍影中馳騁,而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成語有“萬變不離其宗”,我是“三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不論日子如何變,改變不了我始終熱愛生活。
- 記者:好報 編輯
- 更多生活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