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中水井的變遷(外一篇)/劉光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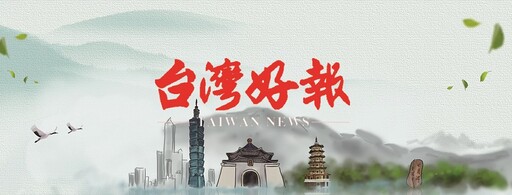
劉光軍
那時候的村子裏面多多少少都會有幾口水井,井自古以來就是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物,它的重要性是毋容置疑的。有井的地方就有人住,就是故鄉。因此井也似乎就成了故鄉的代名詞。當人們為了生活而外出的時候,人們往往就會用“背井離鄉”去形容。人活在世上,吃飯喝水是時時刻刻都離不了的事情。因此,水井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自古使然。
我的家鄉也不例外,每條街上都會有水井,比較長一點的街道上還會有兩口、三口。人們做飯飲用需要它,洗衣喂牲畜需要它。在每一口井上都安裝有一架轆轤,人們需要用水的時候,就挑著水桶來到井上,然後搖動轆轤開始汲水。水井是村裏人兌錢自己掏的,那時地下水很淺,向下挖不到一丈深就會見水。水質也好,口感也好,又沒有污染。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看到家裏的水缸裏沒有水了,就會挑起水桶去打水。一般需要往返好幾趟才會把水缸挑滿。那時候沒有洗衣機等設備,洗衣服全靠手洗,所以也不會浪費太多的水。挑滿這麼一缸水,往往可以吃上一兩天。
後來,隨著地下水位的下沉,井裏的水也就不夠用了。這時候人們就會在井裏繼續向下挖,加裝“二道盤”。這時候的井就會變得很深,用轆轤打一次水需要很長時間,特別費勁。再後來,人們只能放棄使用這種人工挖成的水井,花錢請來專業的打井隊,打出三四十米深的機井。這種井不能再用轆轤來做汲水工具了,只得安裝上“深水泵”,改用電做動力,抽上來的水還需要修建一個大水池子儲存。再在水池的四周安裝上水龍頭。這樣,村民不管是什麼時候來取水都可以打到水,十分方便。雖然還是需要用扁擔挑著水桶來打水,但不用再費力搖轆轤,一擰龍頭就可以接水了,人們也很開心。
剛弄好的幾天裏,水池旁邊很熱鬧,人們紛紛趕過來跳水,人多的時候還排起了長隊等待。一時間,人們的說笑聲、扁擔上鐵鉤子的撞擊聲、水桶的碰撞聲和著水龍頭嘩啦啦的流水聲,組成了一曲特別的“交響樂”。聽著就讓人那麼開心。我家門外就是水池子,所以我打水從不用扁擔挑,接滿了兩桶水,兩手一提就到了家。看著別人羡慕的眼光,我心裏也很得意。
這樣大約持續了四五年的樣子,眼瞅著上水量又變得越來越小了,只好再請來打井隊,鑽上一口七八十米的深井,這次“深水泵”是不能用了,又換上了“潛水泵”。並且每個井上都配備了一個帶有增壓裝置的大鐵罐,然後挖溝把引水管接到了家家戶戶。也就是說,家家戶戶都安裝了“自來水”。雖然不是24小時有水,但從此以後就告別了挑水吃的歷史,吃水用水幾乎和城裏一樣方便了。
再後來,政府說是要實行統一供水,建立了供水站。吃上了24小時不間斷供水的自來水,水質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從此以後,村民的吃水問題就徹底的解決了,再也不會為吃不上水而發愁了。聽說,以後還會吃上“南水北調”的長江水,不知是真是假,心裏盼著想著就是了。
◆媚好鄉音
在我家鄉一帶的土語中,在所有帶“了”的詞中“了”都被讀成了“老”。如:“把它吃了”就會說“把它吃老”,“把這碗水喝了”說成“把這碗水喝老”“停了”說成“停老”等等。再有就是所有帶子的詞語中的“子”都通通被讀作“的”。比如桌子讀成桌的、椅子讀作椅的 ,讀人名也是這樣,我老婆叫淑梅,偏偏丟了淑字,只取一個梅字,那就叫“梅子”吧,偏又叫成“梅的”。她一出門,有人看見她就打個招呼“梅的,吃了沒有?”,另一個人也許會問:“梅的,去做啥呀?”老人如此叫她,平輩兒的年輕人也這樣叫她。別人不知道,反正我聽到別人這樣叫她,總感到有一種莫名的親切的感覺。這也許和我的愛好有關吧,我愛寫詩詞,而寫詩詞的人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總有解不開的濃濃的鄉愁。尤其是一落生就耳濡目染的鄉音,更是深入了骨髓,親切,中聽。所以每當讀大詩人賀知章的《回鄉偶書》時都會不由自主地就紅了眼圈兒。是啊,“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就是詩人,這就是一個離開家鄉一輩子、什麼都會改變,而鄉音卻無從變化的詩人。雖然生活中不是人人都是詩人,但這種與生俱來的鄉土情懷卻都是一樣具備了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有過這樣一種感覺:就是有的時候當你用普通話或別的什麼一種語言去表達一種情感的時候,往往會偶爾出現一種暫時的表達障礙,這時候,你就會不自覺的把它切換回自己的鄉音。並會真切的感受到用鄉音表達的流暢和愉悅。
鄉音不僅僅是一種語言,更是一種古老文化的傳承。不僅僅是一種地域的符號,還更是一種祖輩基因的遺傳。你可以在外面用普通話、用英語、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去交流、去學習、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但是,當你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回到了自己溫暖的家裏,當你的面前只是你的父親、你的母親、你的孩子和你最親最近的人的時候,鄉音就會成為你們之間唯一的用語。自然、和諧。說著它,就似乎能和祖輩對話,就能夠理清自己的血脈。就能得到在外面永遠也得不到的慰藉。
我這輩子沒幹別的,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教書。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教書匠在工作的時候必須要使用普通話。這也是教師唯一的職業語言。如果一個教師在工作的時候不使用普通話無疑是違反職業紀律的。為此,我們都會考取一個普通話等級證書。就算是這樣,我在上課的時候還是習慣使用鄉音。不是我駕馭不了普通話,而是我總覺得只有用鄉音才會有感覺,才能無拘無束流暢快樂地表達一切,才會毫無羈絆的和學生進行溝通。不僅如此,就是平常和朋友一起的時候也不習慣用普通話,自己對那種交流的感覺是陌生的,好像是身處異鄉,有一種遊子的感覺,很陌生,也沒有安全感。尤其是聽了那些個帶著方言土語的所謂的“普通話”的時候,聽著聽著就會感覺很彆扭。因為違和的都不會是愉悅的。
我們這邊的鄉音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語速,實際上是對詞語的省略。這個特點是最讓外地人頭疼的。他們第一個感覺就是“你們說話太快了,聽不懂”。沒錯,就是因為我們在說話的時候喜歡省掉一部分字所造成的。其特點是,某些詞的快速兒化的特殊發音。比如,媳婦一詞,就讀成了“siu兒”,大北汪讀作“大biang”,回來,讀“huai”,做啥,讀“雜”等等。我因愛好詩詞創作,深入接觸過古時候詩人作詩的時候所必須遵循的基本韻律——“平水韻”,竟從中無意中發現一個秘密,現存鄉音中竟會有很多詞語的發音,與古時候“平水韻”中的發音相近或相同。比如“平水韻表中的”上平十灰裏的“回”就應讀“【音】:懷”。在家鄉,每當遇見從外面回來的人打招呼時就會問對方:“你啥時候huai(音:懷)的?”所以,你守候鄉音,就等於你守住了自己的根,這話一點也沒有錯。
- 記者:好報 編輯
- 更多生活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