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片戰爭:矽時代的新賽局,解析地緣政治下全球最關鍵科技的創新、商業模式與台灣的未來 (下) /天下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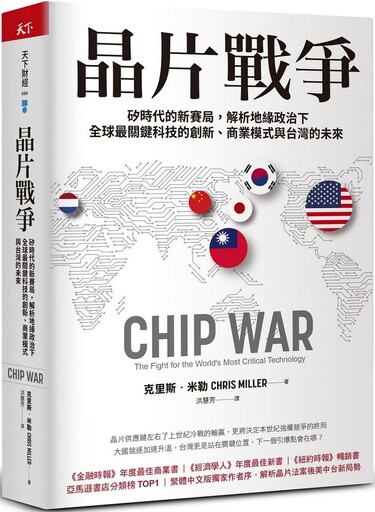
晶片戰爭:矽時代的新賽局,解析地緣政治下全球最關鍵科技的創新、商業模式與台灣的未來
★內文試閱:
2020年8月,馬斯廷號往南航行時,世界才剛開始意識到我們對半導體的依賴,以及對台灣的依賴。我們每年使用的新運算力中,有三分之一是來自台灣製造的晶片。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先進的處理晶片,都是由台灣的台積電生產。2020年,當新冠病毒席捲全球時,晶片業也受到衝擊。一些工廠暫時關閉,車用晶片的採購量大幅下滑。隨著世界各地許多地區準備在家工作,個人電腦與資料中心的晶片需求大幅飆升。接著,2021年,一連串的事件又導致上述供應鏈中斷的現象加劇:日本一間半導體工廠失火;德州發生冰風暴(那裡是美國的晶片製造中心);馬來西亞開始新一輪的新冠疫情封城(許多晶片是在馬來西亞組裝及測試)。突然間,許多離矽谷很遠的產業都面臨嚴重的晶片短缺。從豐田(Toyota)到通用汽車(GM)等大型汽車製造商都不得不關廠數週,因為他們無法取得需要的半導體。即使是最簡單的晶片短缺,也會導致地球另一端的工廠關閉。這一切彷彿是全球化出問題的完美寫照。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歐洲、日本的政治領導人從未多想過半導體。他們就像一般人一樣,以為「科技」指的是搜尋引擎或社群媒體,而不是矽晶圓。
當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與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問道:為什麼他們國家的汽車廠關閉時?
答案隱藏在錯綜複雜的半導體供應鏈背後。一個典型的晶片,可能是一個加州與以色列的工程師團隊,使用美國的設計軟體,根據總部位於英國、軟銀集團旗下的ARM公司的藍圖設計出來的。設計完成後,會送到台灣的工廠,那家工廠從日本購買超純矽晶圓及特殊氣體,接著利用全球最精密的機器,把前述設計刻在矽上。那種精密機器可以蝕刻、沉積、測量幾個原子厚度的材料層。這些工具主要是由五家公司生產,一家荷蘭公司、一家日本公司與三家加州公司。如果沒有這些公司,基本上不可能製造出先進的晶片。之後,晶片會經過封裝與測試,通常是在東南亞進行,然後才運到中國,裝進手機或電腦。
如果半導體的生產過程中有任一步驟中斷,全球新運算力的供給就會受到威脅。在人工智慧時代,大家常說資料是新石油。然而,我們面臨的真正限制,其實不是資料的取得,而是資料的處理力。儲存與處理資料的半導體數量是有限的,生產半導體的流程極其複雜,而且成本高的可怕。石油可以從許多國家購買,但運算力不一樣。運算力的生產,根本上是取決於連串的關鍵控制點:機台、化學物、軟體。這些通常是由少數幾家公司生產,有時甚至只有一家公司生產。經濟上找不到如此依賴那麼少公司的產業了。台灣的晶片每年提供全球37%的新運算力;兩家韓國公司生產全球44%的記憶晶片;全球所有的極紫外光(EUV)曝光機都是由荷蘭的ASML製造,沒有這些機器,頂尖的晶片根本不可能製造出來。相較之下,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產油量占全球產量的40%,那看起來就沒什麼大不了了。
這個遍及全球的公司網絡,每年生產上兆個奈米級的晶片,可說是效率的極致,但也是驚人的弱點。新冠疫情的衝擊讓我們有機會窺探,萬一地震剛好發生在這些地方,那對全球經濟可能造成多大的影響。台灣位於斷層線上,1999年那條斷層線曾引發芮氏7.3級的地震。幸好,那場地震只讓晶片停產了幾天。但台灣發生更強烈的地震,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毀滅性的地震也可能衝擊日本與矽谷。日本是地震頻繁的國家,日本生產的晶片占全球產量的17%。矽谷現在生產的晶片雖然很少,但生產晶片製造裝置的工廠就設在聖安德列斯斷層上。
不過,如今最危及半導體供應的巨變並不是板塊碰撞,而是強權之間的衝突。中國與美國爭奪霸主地位的同時,雙方都把焦點放在掌控電算的未來上,而且可怕的是,那個未來取決於一個小島,中國認為那個小島是個叛離的省份,美國則已經允諾以武力保衛它。
美、中、台晶片業之間的相互連結極其複雜,令人眼花繚亂。找不到比台積電創辦人更適合說明這點的人了。
截至2020年,台積電還把美國的蘋果與中國的華為視為兩個最大的客戶。張忠謀生於中國,二戰時期在香港成長,後來在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史丹佛接受教育。他在達拉斯為德儀工作期間,幫忙建立了美國早期的晶片業。他獲得了美國最高機密的安全許可,為美國軍方開發電子產品,並使台灣成為世界半導體製造的中心。中國與美國的一些外交政策的策略家,夢想著讓兩國的科技業不再有牽連。但是像張忠謀這樣的人幫忙建立了一個由晶片設計師、化學品供應商、機台製造商所組成的超高效率國際網絡,這個網絡是不可能輕易解體的。
當然,除非有什麼東西爆炸,那就另當別論了。中國明確表示,絕不排除武力犯台以追求統一的可能。但它不會採取兩棲攻擊那樣戲劇性的手段,而導致半導體引發的震波席捲全球經濟。即使中國軍隊展開部分封鎖,那也可能引發毀滅性的破壞。對台積電最先進的晶片製造廠發動一次導彈襲擊,就可以輕易造成成千上百億美元的損失(把手機、資料中心、汽車、電信網路、其他技術的生產延誤成本加總起來,就非同小可)。
讓全球經濟受制於世界上最危險的政治爭端之一,似乎是一個可能在歷史上留下記錄的重大錯誤。然而,先進的晶片製造集中在台灣、南韓、東亞的其他地區並非偶然。政府官員與企業高管連串深思熟慮的決定,創造了如今這些遍及全球的供應鏈。亞洲龐大的廉價勞力資源,吸引了尋找低成本勞力的晶片製造商。該區的政府與企業利用海外的晶片組裝廠,來學習並最終開發出更先進的技術。美國外交政策的策略家把複雜的半導體供應鏈,視為把亞洲與美國主導的世界綁在一起的工具。資本主義對經濟效率的持續要求,促使業者不斷地削減成本,也促進企業整合。摩爾定律背後的穩定技術創新,需要更複雜的材料、機械與製程,那些東西都只能透過全球市場供應或資助。我們對運算力的龐大需求只會持續成長。
這本書引用三大洲(從台北到莫斯科)的歷史檔案研究,以及對科學家、工程師、執行長、政府官員的上百次採訪,主張半導體定義了我們的世界,決定了國際政治的形態、世界經濟的結構與軍事力量的平衡。然而,這種最現代的裝置有一段複雜又充滿競爭的歷史。它的發展不僅是由企業與消費者塑造的,也是由雄心勃勃的政府與戰爭的迫切需要推動的。想要瞭解這個世界是如何變成由無數個電晶體與少數幾家不可替代的公司界定的,我們必須從回顧矽時代的起源開始看起。
>>內文試閱(上)>>內文試閱(中)
>>內文試閱(下)
- 記者:王穎心|PChome新聞特派記者
- 更多財經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