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老媽的自信/夏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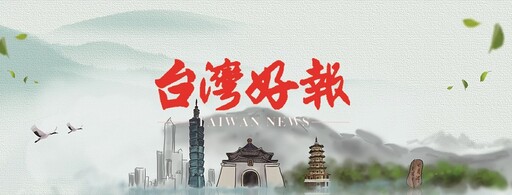
夏俊山
清明節回家,老媽跟我聊了幾句就開始感歎:“唉,不中用了。我已經完全不中用了,就是個廢人。”
她滿臉自卑的神情,讓我一時間摸不著頭腦。 “什麼不中用了?哪個給你佈置任務了?”詢問之後,我才明白:原來老媽見我回家,先是下廚房燒了幾個我愛吃的菜,後來又檢查我的衣服,發現有一顆鈕子快要掉了,就找出針和線,想把鈕子加固釘牢,結果,穿針就是穿不上。老媽年輕時飛針走線,做衣服的手藝在我們生產隊還是有些名氣的,現在穿針穿不了,她產生了嚴重的挫敗感,於是感慨:不中用了,是個廢人,語氣中充滿了自卑。
老媽呀,你92歲的生日宴都過去快兩個月了,你還想繼續飛針走線嗎?不要說你,我才70歲,已經要配眼鏡了,否則,穿針肯定也穿不了。歲月不饒人。老媽這樣的年齡,生活自理,還能種一些蔬菜,家裡吃不完,還經常送給我妹妹,已經很不錯了,怎麼能說是“廢人”呢?
有人說:“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其實,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沒有比較就不知道誰厲害。”聯想到老家,老媽生活多年的楊舍大隊13生產隊(後改稱13組),90歲以上的就老媽1人,一些70多歲、80多歲的,身體還不如老媽。例如我的嬸嬸馬桂芳,85歲就需要人照料。今天回老家祭祖上墳,讓老媽跟我一起,回到鄉下老家,串串門,跟老鄰居聊聊家常,有了比較,她就知道了:92歲,能自己買菜、種菜,思維清晰,行走自如,哪裡是“不中用”?應該是“很中用”!甚至可以說是“很厲害”。
我講了一起回鄉下老家祭祖的想法,老媽立刻就答應了。她還準備了不少禮品,又下樓轉了一圈,買了好幾斤肉,說是送給我的嬸嬸,比包裝漂亮的食品實惠。
老家在海安市西北的墩頭鎮新舍村,午飯後,我和老媽都沒有休息,妹夫開車,直接帶著我們回到了當年的13生產隊。我在生產隊種地時,全隊33戶,133人。如今,人口只剩下一半多一點。下車後,看著眼前熟悉又有些陌生的風景,老媽的眼神一下子亮了起來,嘴裡開始念叨幾十年前的往事。
曾經的小路如今變成了水泥大道,隊長孫慶山,管理生產隊還是有一套的,50多歲就去世了;隊長張啟榮,生產隊的特等勞力(那時男女社員叫男勞力、女勞力。勞動按評定的等級記工分),去世的時候,好像不到80歲……老媽念叨的那些人,我也熟悉,年齡都比老媽小,健在的,身體也不是很好。都說人不能比人,老媽跟那些人一比,不但自卑感沒了,甚至還有些自豪。
沿著田間的土路,我們向祖墳走去,油菜花已經盛開,像是給大地鋪上了一層金色的地毯。空氣中彌漫著芬芳與春泥的氣息,這是故鄉特有的味道,老媽貪婪地呼吸著,仿佛要將這些熟悉的氣息深深地刻在心底。
沿著一條土路,來到了祖墳前,老媽腳步變得格外莊重,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慢慢地走到了墳前。我輕輕地蹲下身子。點燃了錫箔折的一袋袋錁兒。老媽低聲念著一些我聽不清楚的話。看著她那虔誠的樣子,我的心中也湧起了對祖先,特別是對父親的思念和感恩。
祭祖完畢後,老媽又急切地想要去看看那些老鄰居。沿著熟悉的路徑走去,一路上,我們遇到了不少鄰居和熟人。老鄰居們看到老媽,眼中也閃著光,他們紛紛圍上來,拉著老媽的手,問長問短。老媽和他們熱情地打著招呼,那熟悉的鄉音、親切的笑容,讓我也感到很溫暖。
老媽還去了娘家——她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如今,父母已在另一個世界。焚化錫箔折的錁兒後,老媽站在娘家的祖墳前,似乎不願離開。我看著她,心裡有些酸澀,又有些溫暖。老媽的根就在這裡啊,歲月雖然帶走了她的青春,但帶不走她對父母的深情。老媽的娘家在雙溪村,走進娘家的老屋,迎面有菩薩、香爐、燭臺、拜墊……海安鄉下民居的堂屋,這種有著濃鬱的傳統色彩的佈置在鄉間很常見,老媽坐在八仙桌後,看著拜墊,好像在默默地回憶往事。70多年前,老媽是這裡張氏家族的一員,19歲時嫁給我父親。
我問正在給我們泡茶的表弟:“這裡的張姓族人,有比我媽年齡大的嗎?”表弟想了想,很肯定地說“沒有”。我對老媽說,你們張氏家族,健在的就數您年紀最大了。
天色有些暗下來,該回城了,老媽有些不舍。她一步三回頭地望著那些熟悉的房屋、田野和老鄰居,仿佛想要把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心裡。我握住老媽的手,告訴她:“媽,你要開開心心,張氏家族,論高夀,數您第一;楊舍大隊13生產隊,論高夀,還是數您第一;您還能走這麼多路,怎麼能說自己‘不中用’呢,看看您的鄰居、熟人,90多歲能自理的能有多少……”
聽了我的一通話,老媽笑了,一副找回了自信的神情。回城路上,老媽靠著我,貼著我的耳朵說道:“這次回來,看到一些老鄰居,我心裡踏實多了。”我知道,她說的“踏實”,應該不只是對過去歲月的深情回望。而是恢復了樂觀自信。
- 記者:好報 編輯
- 更多生活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