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克朗棋(外一篇)/劉光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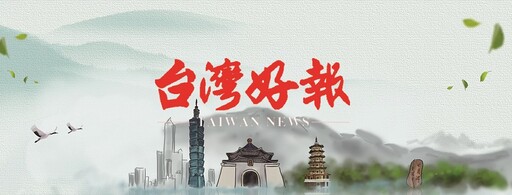
劉光軍
1979年的時候,我正在邯鄲上學。那時候的學校,課餘時間也沒有什麼可玩的東西。電視也只有到了星期日的晚上才能看,全學校也就只有那麼一臺破舊的黑白電視機。平常下了晚自習或是到了星期天,總會感到有些無聊,我還比較好一點,因為我天生好靜不好動,得住寂寞,還有就是我特別愛看書,所以大部分的空餘時間,都可以泡在圖書館或閱覽室裏。其他的同學可就不一樣了,他們就會想方設法尋找一些娛樂的方式。不是三五成群的出去瞎轉悠,就是悶在宿舍裏睡大覺。直到有一天,我們宿舍的幾個人,也不知道從那弄來了一個新鮮玩意,我連見都沒有見到過,更不用說它的名字了。第一眼看到它我還以為是象棋,後來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什麼象棋,而是一種連聽都沒聽說過的“克朗棋”。
那時候正是夏天,天氣很熱,大家在宿舍裏都喜歡光著膀子。我先是看他們玩,後來我也參加了進去。誰知道不玩還可以,一玩起來還上了癮。這個原本是由幾個老師玩的,先是有幾個同學看他們玩,後來也不知怎麼的就弄回了宿舍開始自己玩,自己玩也就罷了,竟還有幾個老師也跟了過來,和同學們一塊玩。甚至有一次就因為玩不過來還動了粗口,差一點就打了起來。現在才知道那時候的人,都喜歡玩這個。
康樂棋其實應該叫康樂球,也叫“克郎球”、“克郎棋”,是類似桌球的一種遊戲,有臺盤和擊杆,也是以將球擊入袋孔為贏。只不過桌球擊落的是“球”,康樂球擊落的卻是“象棋子”。所以大家都把康樂球形象地稱為“康樂棋”。比賽時,用棋杆撞擊母棋,母棋與目標棋子碰撞後,目標棋子進洞者獲勝。雙方輪流射棋,目標是將敵方的棋全部射入洞中。
據說在印度殖民統治時期,駐印度的英軍官發明了桌球,不久從印度傳到中國。是不是模仿桌球的康樂球也跟著傳到了中國呢,還是中國人見了桌球而自製了康樂球呢,現在還沒有可以肯定的說法。
上海開埠較早,也是國內早早有康樂球的。
有位老上海說早年老北站附近的康樂路上,一家木器店老闆製作了擊打象棋子進洞取樂的木質方盤。當時參與的人都覺得很好玩,為了說話方便,就以路名來給這玩意兒起了名,在康樂路上打球成了打康樂球。這也許就是康樂球名稱的來源吧。
還有一種說法是上世紀50年代,香港兒童人口上升,相應的社會服務、玩樂設施的需求隨之增長。但那時香港社會尚未普遍富裕,兒童多自製玩具,瓶蓋、折紙、糖盒都是玩具,“麻鷹捉雞仔”“何濟公”等是人人都玩的遊戲。60年代以後,香港為兒童興建遊樂場地,並組織各種兒童活動。香港製造業起飛,成為玩具王國,康樂棋就是這個時候出來的。
康樂棋在中國最早出現的時間,有據可查的是1962年晚秋,法國攝影師 Rene Burri在河南洛陽農村拍攝照片。60年代的洛陽農村,正是人民公社時代,一群孩子無憂無慮地在玩耍。其中幾個稍微大一點的孩子在玩康樂棋。攝影師抓拍了瞬間,這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康樂棋照片了。
康樂棋盤看起來不大,邊長也就90-100釐米,但其實玩起來還是需要一定的運動量,對身心健康很有益處,大家都很喜愛這種休閒活動。那個年代,桌球是貴族的遊戲,而康樂球當然是平民的遊戲了。
雖然康樂棋售價沒有桌球貴,但對當時的國人來說,買一整套也要花不少錢,所以動手能力強的父輩們就找來木料,自己做臺盤和擊杆,擺上象棋子,就可以玩了。並且在臺盤中央畫上象棋盤,擊打棋子玩累了還可以下象棋。因為具備雙重功能且成本低,康樂棋在七十年代後期一下子風靡全國,幾乎每個機關單位國企單位的娛樂室裏,都備有康樂棋供大家娛樂。
對老一輩人來說,在那個缺乏娛樂的時代,康樂棋帶給了他們無限的歡樂。
隨著經濟發展檯球的普及,康樂棋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似乎銷聲匿跡,只留下夢幻的回憶。許多老人對此唏噓不已。但其實,康樂棋近些年又回流了,這得益於印度人對康樂球一直的堅持,印度還經常舉辦各種康樂棋比賽,邀請各國人士參與。
畢業後至今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了,再也沒有見過有誰玩過這樣的遊戲,就連做夢也沒有夢到過。似乎這個世界上它們就像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似的。直到有一天我想寫點東西,才從我的遙遠的記憶裏尋找到了它們,又重新讓它變得清晰起來。
◆一個鄉村校長的“改革”
世上的事原本就沒有什麼道理。正如有些人總愛把自己太當回兒事,而事實上卻根本不是那回事兒一樣荒唐可笑。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社會上開始流行改革,似乎什麼都要改一改才過癮。有些人也忘了自己幾斤幾兩,就要憑著自己手裏一丁點權利揚言也要搞什麼改革。說白了就是想在上司面前顯擺顯擺,出出風頭。比如當時就有這麼一位鄉鎮的中心校長,就挖空心思的想搞出一點名堂來為自己提提身價。於是就搞了一出讓人噴飯的鬧劇。
這一天,他把全鎮教師的備課本全都收了起來,然後帶著幾個人一起來到鎮裏的大馬路上,擺好幾張桌椅,拉上一條橫幅。上面寫著“某某中心校歡迎監督
諮詢提意見”。他設想這樣一搞,肯定會有很多人來互動,為此他還準備了照相機,想好好地把它利用一下。同時還用大喇叭反復不停地做著廣播宣傳。因為這一天正好是鎮上趕集的日子,十裏八鄉的人都會在這一天來鎮上趕集上會。他單單挑選這樣一個日子,也是動了一番心思的。
誰知道正應了這麼一句話“想像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鬧了半天,從始至終都沒有一個人上前諮詢,更別說提意見了。集市上人流湧動,熙熙攘攘,可他們都在做著自己想做的事,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裏還有一個很另類的交易攤子。他們幾個尷尬的坐在那裏,被火辣辣的太陽烤著,呆呆地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估計這時候他們的心是崩潰的,哭的心思都有了。
老師們看到如此景象,都說這些人是沒事找事,吃飽了撐的。他們也太把自己當回事兒了,活該丟人現眼。
另外,在一個詩詞群裏,經常會邀請一個所謂的大師來舉辦詩詞講座,在群主和一些喜歡跟風的人的大肆鼓動下,一時間人頭攢動,聽者如雲。我也忝列其中,只聞阿諛諂媚之聲不絕於耳,馬屁拍得山響,紅包如雨亂落,不用說這個所謂的大師也大大的發財。這其中唯有我一個另類,一不奉承,二不舍財,還喜歡挑毛病。當聽到大師將“羸弱”說成“贏弱”時,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去糾正他。可能是他們有些忌憚大師的名頭太大,也可能是給大師留一些面子,但最有可能的還是他們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大師讀錯了。我卻不然,既然讓我聽出來了,我就必須立馬給他糾正,我才不管什麼大師不大師,面子不面子的。如果真是大師,又怎麼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呢?於是,我毫不客氣的發信息給他,指出他的錯誤。大師倒還不錯,時間不大就回復了過來,“是我老眼昏花弄錯了”。是老眼昏花還是胸無點墨,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就算是老眼昏花,看字不清,誤把“羸”字看成了“贏”字,可你既然稱作大師,你聽說過有“贏弱”這個詞嗎?分明是自己無知,卻硬要拉年老墊背,這也太讓人無語了吧。就算是主持人心存異謀,那你自己也應該有點自知之明吧,你就不會推辭或是謙虛一下,分明是太把自己太當回事兒了,才會當眾出醜,若人笑話了。
還有一位名氣很大的大師,據說也收了不少的徒弟。整天沉迷於那些所謂的徒弟們的阿諛奉承之中,搖頭晃腦,自覺已經有了些“王氣”,就差稱“萬歲”了。回過頭來再看看他的那些所謂的大作,字裏行間無一不透露著一股股戾氣、怨氣,一首首讀起來面目可憎,毫無美感。他極力反對個人崇拜,卻自己特喜歡別人吹捧,殊不知其虛偽本質和偽善面目早已經暴露無遺。他的那些所謂的詩,意足而境疏,充斥著無限的議論和說教,再不就是謾罵與諷刺,陰氣極重。讀者看到的永遠是翻滾的烏雲和陳腐的枯草。似乎在他的眼裏根本就不存在鮮花,沒有陽光、白雲和藍天。更沒有親情、愛情和柔情。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個“鬥士”,而他的所作所為卻又像極了一個無賴。由此看出,這個人的心裏是有多麼的陰暗才能這樣啊!夜郎自大,井底之蛙。他也太把自己當回事兒了吧。
由此看來,做人不僅要踏踏實實,還要低調一些為好,尤其是你在最走運的時候,更需要如此。
- 記者:好報 編輯
- 更多生活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