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初體驗/馮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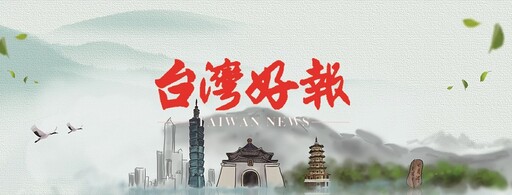
——我的訪學劄記
馮兵
終於辦妥了赴臺灣中央研究院訪學的所有手續。走的那天,因為某種原因航空管制,原訂上午8:45從廈門高崎機場出發,結果拖到9點半過了飛機才得以起飛。在飛機上,我頭靠著舷窗,本想看看臺灣海峽,卻在不經意間睡著了。等我醒來往舷窗下一看,無邊無際的海撲入眼簾。在一朵朵棉花般的白雲下,那一片無垠的灰藍色海洋就像一張碩大無朋的地毯,寧靜安詳,完全不是想像中的大洋的模樣。沒有湧動的海浪,我似乎只看見了地毯上綿密粗獷的、被人經年累月踩實了的毛線紋路,雖然偶見貨輪和白色浪花嵌在上面,也只是仿若孩童的小玩具和他們吃飯時撒在灰藍色地毯上的小飯粒。
漸漸的,視野中出現了幾個綠色的小島,此時飛機的高度也下降了,放眼望去,耀眼的陽光下,蔚藍的天空、潔白的雲朵、深藍的大海、濃綠的小島、深黃色的島岸、銀色的淺灘、推湧著的簇簇浪花,交織成了一幅美得令人窒息的風景。緊接著,飛機似乎轉了個彎,機翼掠過遠處的一個海濱小城,在機身下方出現了農田、海產養殖場、兩三層高的民房、道路和疾馳的車輛,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和大陸城市的郊區好像!
飛行差不多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飛機就降落到了臺北桃園機場。隨著飛機落地後的緩緩移動,我透過舷窗觀察著機場:老舊的停機坪、灰撲撲的房子、大陸各家航空公司的飛機,卻沒有見到其他國家的飛機,也許是因為有不同的分區吧。和大陸內地的機場相比,桃園機場是不大起眼的。當飛機最後停穩的那一刻,我終於看見了“臺北桃園機場”的繁體字標牌,這時才算是真切地意識到:我到臺灣了!
在赴臺的頭一天,中研院的蔣小姐就已經在郵件裏告訴了我下飛機後該如何搭車,並幫我在學術活動中心預訂了兩晚的客房。由於知道桃園機場到“中央”研究院較遠,所以我也就沒有考慮打車的問題,而是依照機場的路標直奔公車(他們叫“公車”)站,結果卻走錯了地方。我在一處公車站牌上找了半天,也沒找到蔣小姐所說的國光43號線,只好硬著頭皮找人問路。早已聽說過臺灣人被求助的時候很熱情,親歷之後發現果然不虛。一個中年人告訴我該去斜對角的售票點買票,在3號月臺上車。他說完看我仍有些茫然,就帶著我一直走到拐角處指給我看明白了,才放心地離開。
買票時,售票小姐說車要12:45分才來,我看了看表,十二點剛過,便有些猶豫要不要改坐計程車(臺灣叫“計程車”)。於是她很善意地說:“要不您先考慮一下,但搭計程車很貴的喲。”年輕的姑娘笑意盈盈,很貼心地為我考慮著,讓我感覺很舒服。在我躊躇的當口,因為拖著行李箱站得離櫃檯有點距離,後面一個男子應招上前去買完票剛要離開時,我說:“小姐,那我還是買吧。”那人這才明白我排在他的前面,當即給我微微俯身連聲道歉,反倒弄得我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臺灣的公車上,陌生的乘客與司機會點頭致意問好、下車時乘客會道謝,這讓我既覺得新奇也頗為感動。車上的顯示幕一直滾動播放著防範打擊人口拐賣的宣傳及報警電話,可見兩岸社會儘管存在各種差異,而人口拐賣卻似乎是共同面臨的問題,我不覺又有些難過。約一個小時後車到終點南港展覽館站,我拖著行李箱哢嗒哢嗒地到街對面攔停了一輛計程車,直赴中研院。
從桃園機場到南港,沿路所見雖然乾淨整潔,但並未看到多少想像中的摩天高樓,然而建築風格多樣,倒也顯出了較濃的現代化氣息。自南港到“中央”研究院的路上,則更是以老舊低矮的房子為主,問過司機才知道,原來這裏是郊區。而南港雖然屬於城郊,卻毫無髒亂跡象,顯得十分整潔有序。
我在中研院的學術活動中心住了兩天,找好房子之後搬到了新的住處。為了買生活用品,先後又乘坐過幾次計程車。其中一個老司機比較開朗健談,他說從沒有出過國,所以沒有去過大陸,老兩口只是到過金門,卻已經很滿足了。因為在臺灣人看來金門是外島,澎湖才是內島,到金門就和出國差不多。至於政治,他很討厭政客們吵來吵去,有話好好講,吵什麼呢?對民眾而言,誰能夠讓臺灣把經濟搞上去,社會安定,那就選誰,誰管你背後有什麼樣的政治主張和意識形態?而且,年輕的一代人更是不會去關心那些政治問題,他們的政治態度更為現實。
可悲的是,對著臺灣我們自稱“大陸”,一些臺灣人卻往往稱大陸為“中國”,把去大陸叫做“出國”(當然也有人會稱“大陸”,稱呼的不同,實際上正反映著他們的政治立場的不同)。對此我一直有些耿耿於懷。基於此,我也試探性地問過那位老年計程車司機對籍貫的看法。他生在臺灣,聽上輩人說自己的祖籍在福建,再往上追溯則到了浙江麗水。但是他說,籍貫這種東西怎麼講呢?比如他自己生在臺北,孫子出生在臺中,問他的孫子“你是哪里人呀?”孫子只會講“我是臺中人”,而不會說是臺北人,更不可能說是福建人。祖籍或籍貫是多麼含糊的概念啊。有一次他在山上看到一座墳塋,墓碑上寫著“某某乃臺北人氏”,他當時卻又笑了:“哪有什麼臺北人,好多年前的臺北哪有人?都是從大陸遷徙過來的!”可是,隨著一代一代的傳衍,年輕一輩越來越沒有了祖籍的概念,對在大陸的先祖認同感、歸屬感越來越弱,他的子女就是典型的例子。聽到這裏,我的心裏有些悲涼,作為兩岸關係重要紐帶的親緣意識在一部分臺灣人心目中越來越淡薄,這顯然並不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所願意看到的。我不由得在內心深處開始認真祈禱,祈禱一衣帶水的兩岸密切合作,親愛一體,永保和平,共同繁榮昌盛!
- 記者:好報 編輯
- 更多生活新聞 »

